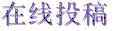1935年3月中旬的一天清晨,赣南山区乍暖还寒。濛濛细雨中的桃江,曲曲弯弯,像一条灰白色的带子飘向远方。
桃江北岸,崎岖不平的山道上,一个商人和一个医生缓缓走来。那商人头戴灰礼帽,身着灰长衫,个子略高,方脸盘,双目炯炯有神。那医生中等身材,面容憔悴,不时朝江边张望。走在他们前面的是几个青年农民,挎着竹筐。这一行数人夹在赶圩的人流里,从从容容地向江边的王母渡口走去。
他们是谁呢?那商人乃是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项英,那医生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那几个青年农民则是项英、陈毅的警卫员。他们今天要从戒备森严的王母渡口闯过桃江去,到赣粤边区的油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一时间,苏区上空乌云翻滚,阴霾层层。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被迫转移。主力红军走后,“左”倾机会主义的幽灵还在苏区游荡,还在危害革命。他们不顾陈毅的反对,仍然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针,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苏区没有保住,红军伤亡惨重,最后被迫分五路突围。项英、陈毅率领一部于1935年3月9日下午6时杀出重围,权衡再三,决定东渡桃江,去赣粤边的油山与先前到达那里的李乐天、杨尚奎部会合,坚持游击战争。
为了减轻部队的压力,缩小目标,项英、陈毅安排剩下的100多名干部战士分散突围,到油山会合。担架队队长曾纪才说:“这一带地形、敌情我了解,正面过桃江敌人封锁很紧,只能绕到上游王母渡过去。”
项英、陈毅带着几个警卫员,跟着曾纪才昼伏夜行,每晚走20多里,一连走了4个夜晚,来到王母渡北岸的王母坑。王母坑是个大村,有上百户人家,曾纪才认识不少人,设法搞来几套合适的便衣,有短袄裤,也有长袍礼帽。他们化了装,准备大白天从桃江渡口混在群众中乘渡船过江。
不料,天亮后传来消息,说白军连长判定昨夜村里来了红军,正开始挨户搜查。陈毅与项英、曾纪才商量:留在群众家里不妥,干脆到江边的茶馆里等待开渡。于是约定,万一在茶馆里谁被查出,其他人不要动,仍按原计划过渡去油山。他们到茶馆里坐下来刚吃了些点心,一个白军军官就带着几个兵进来。白军军官扫视每张茶桌,眼光在茶客脸上转来转去。当他来到陈毅坐的那张桌子时,陈毅站了起来,微笑着向他递烟让坐。白军军官点燃烟,边吸边问:“哪里来?”“里山。”“到哪去?”“过江行医。”
陈毅听他是广东南雄口音,也就有意地露出几句南雄土语。陈毅虽是四川人,但对广东的客家话不但能听懂,而且能说上几句。他曾几次到南雄开辟游击区,学会了一些南雄土语。白军军官一听陈毅会说南雄话,口气马上缓和下来,长脸也变成了圆脸,笑着说:“你是南雄人?”陈毅和颜悦色地回答:“在南雄行过几年医。”“那我们是同乡了!幸会!幸会!请问贵姓?”陈毅一抱手:“免贵。小姓刘。请问你——”白军军官说:“我姓牛。再见。”说着就往项英坐的那张桌子走去。陈毅为项英担心,他是湖北武昌人,不会说赣南话,敌人问话就麻烦了。幸好白军军官只是向项英扫了一眼,就走出了茶馆。
敌人一离开茶馆,陈毅马上让警卫员张德胜提起药箱,又向大家使个眼色。项英连忙用长衫的袖子掸了掸礼帽,跟陈毅出了茶馆,向江边渡口走去。这时已是早上7点多钟。去江南赶圩的人很多,卖鱼的、卖鸡鸭的、卖柴卖茶的都有。陈毅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今天人多,敌人不可能细查;担心的是他曾率红二十二军司令部在这一带驻过,和老百姓很熟,要是有人认出“陈军长”来,可就麻烦了。一路上,陈毅尽量把帽檐往下拉,可是很多老表还是不时地向他打量,有的甚至吃惊地睁大了眼睛,张开了嘴巴,但谁也没有讲话。有的老表显然看出陈毅、项英不是本地人,是那边(指苏区)过来的,可是没人多嘴。
陈毅、项英混在老百姓里正向江边走着,身后突然传来了“刘医生、刘医生”的喊声。由于陈毅是第一次化装成医生,加上一心想着渡江可能发生什么麻烦,就没有注意后面的喊叫,直到袖管被人抓住,才猛然醒悟过来。陈毅转过脸来一看,是在茶馆里跟随白军军官检查的一个粤军上等兵。
“你耳朵好沉哟,我叫你好多声,怎么听不得?”
陈毅连忙道歉:“实在对不起,我耳朵是有些沉。听你口音,好像也是南雄人?”
“可叫你说对了,我是南雄大树下人,和我们牛连长是同乡。今天下午营长要来检查防务,我们连长叫我过江多买些酒肉,可是钱只给我……”
“呀,这没关系,我们是同乡,过了江,缺多少,我给添上。”陈毅故意把口袋里的银元搞得叮当响。
上等兵满脸是笑,连声说:“我代表连长谢谢你啦!当兵的都是穷光蛋,苦得很哟!”
说着,他们已来到渡口,过渡的人很多,拥挤着站满了码头。尽管江上雾气濛濛,看不清南岸,但人们还是不安地睁大眼睛向南岸眺望。粤军为了对江北游击区进行封锁,把所有的船只都扣留在南岸,每天只放一条船来回摆渡。说是8点钟开渡,其实要看守渡口的那个粤军排长起得早晚,高兴还是不高兴。
这天还好,陈毅他们来到北岸渡口不久,船就开过来了。南岸到北岸来的人不多,很快下完。项英急着上船,陈毅轻轻拉住他,小声说:“先上船的后上岸,后上船的先上岸。先上岸的搜查严些,我们当中上岸,万一被发觉,就可以冲上岸去,向街里跑,到油山会合。”
渡船缓缓地离开了岸边。由于船上人多,船老大虽然年轻力壮,把茶碗粗细的竹篙撑得像弓,船却好像不动似的,大约十多分钟,才来到江心。南岸影影绰绰映入了陈毅的眼帘:陡峭的山崖,近于垂直;不大的码头,有粤军设下的关卡。
渡船快靠岸时,陈毅发现码头出口处贴了两张3尺见方的大画像。一张上写“陈毅”,一张上写“项英”,画像两旁还写着醒目大字:“捉住赏洋5万元!”粤军排长领着士兵,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即将靠岸的渡船。
陈毅、项英苦苦思索办法,不知不觉渡船已靠上了南岸码头。敌人就在眼前,画像近在咫尺,在人们争先恐后向出口涌去的时候,陈毅小声对项英说:“按原计划办。”那个粤军上等兵不顾先后次序跳上了岸等着陈毅,张德胜也挤了上去,把陈毅接到岸上。
陈毅看上去倒是很坦然,和那个上等兵肩并肩地夹在人流中边说边走。“在这里的弟兄们你可熟悉?”陈毅试探地问。那个上等兵摇摇头回答:“谈不上熟。不是一个连的,就是每次上圩,碰鼻子碰脸的,流水的交情。”陈毅拍了拍他的肩头,塞给他一块银洋,暗示着说:“你我都是自己人。”
说着,他们已来到了出口处。陈毅让那上等兵走在他和张德胜的前头,为的是趟趟路,挡挡风。到了卡子口,粤军排长什么也没问就让那上等兵过去了。上等兵特意回过身来招呼陈毅与张德胜。张德胜当然和画像对不上号,那个粤军排长却盯上了他挎的那个“药箱”。陈毅连忙笑吟吟地冲着排长说:“长官,请查看,都是一些丸散膏丹。”说着,掏出一包哈德门香烟,塞给了粤军排长。粤军排长的黑眼珠在画像和陈毅脸上来回转动了两次,头一摆,放过了。
陈毅担心项英会遇到麻烦,故意放慢脚步,向后望去,只见两个警卫员紧跟在项英身后,看样子是要随时准备架起他夺路冲出去。粤军士兵从上至下搜了一遍项英的全身,放行了。可是项英刚朝陈毅这边走过来,粤军排长突然挡住去路:“慢着,你在画像前站一站。”项英做过多年的地下工作,很有些应付敌人的经验,他沉着自如地面对画像站着,粤军排长的眼光在画像和项英脸上扫来扫去。项英望着画着自己模样、写着自己名字的画像,面不改色。粤军排长竟然当面错过,头一摆又放行了。
陈毅见项英脱险了,就示意曾纪才继续带路向前走。他们一气走了40里,才在一个树林里坐下来休息。张德胜惊奇地问陈毅、项英:“敌人把你们的像画得那么大,怎么面对面就认不出来呢?”陈毅微笑着问:“你看画得像我们吗?”“我明白啦!画像上你们两个都胖。”“哈哈!这几个月我们都瘦多了!”陈毅大笑了起来:“敌人要是用传单上的照片对着检查,还可能认得出来。可是他们发财心切,把照片放大了几十倍,画得又太差,帮了我们大忙啦!”
项英见警卫员们还不明白,就说:“你们看看,我现在是长方脸,可他们画成了什么样子?大胖圆脸,还戴着眼镜,可我现在没带眼镜吧!”
陈毅说:“是的,把老子的尊容也改了,我眉毛往上扬,可他们画成两把竖起来的黑扫帚!我嘴阔,可没有阔到两耳,占去面孔的三分之二啊!哈哈……”
项英没有笑,他说:“今天也有个教训,敌人对你们的检查就没有对我和老刘(陈毅在三年游击时期的代号)严。看来我们这身行头显眼了点,要重新化装。”
于是,曾纪才又想法买来两身半新不旧的衣帽,请陈毅和项英换上。只见他们头戴灰色毡帽,身穿藏青色的紧身棉袄,黑裤子下面露出一双布织草鞋。这是地地道道的赣粤边普通农民的装束。陈毅半开玩笑地说:“啊,旧的生活结束了,新的生活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