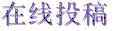1985年8月15日的太阳特别辉煌,它照耀了我的心灵也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它的光芒像一支支利剑,刺痛了我的心脏也刺激了我的神经。
这天上午,我骑着自行车从北京东路往鼓楼前进。到北极阁,忽然发现路边聚集着很多人。多年的记者生涯驱使我关注热点消息。我下车一看,路边的绿树花丛不见了,只见一堵花岗岩石碑矗立眼前,正面黑色大理石上镌刻着一行长长的金色隶书: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北极阁遇难同胞纪念碑
人们在石碑前肃立着、凝望着、沉思着。我被这场景震惊了:这块花草繁茂的绿地,怎么会是日军杀人的屠场呢?
这天的《南京日报》报道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南京市在当年侵华日军集体屠杀南京军民的遗址上,建立了十三块纪念碑。我激情难抑:胜利是用鲜血换来的!于是有了冲动,我想写一首诗:《石头城,站起来十三个石头人》。
五分钟的狂热过了,诗没有写出来。过了几天,朋友们一起聊天。有人说:“钱钢写了《唐山大地震》,你也来个大的吧!”“我写什么呢?”
“南京大屠杀!”有人说。
像电光石火。一句话,又点燃了纪念碑前的激情。
我立即查阅史料。很遗憾,我没有找到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具体材料,一些史书上只是简要的概述或几百字的条目。问了一些人,都支支吾吾,或一知半解。
不知道的事情应该让大家知道。
我觉得,这是一段不该忘却的历史。
于是,我开始了茫茫人海中的寻找。快半个世纪了,当年二十岁左右的亲历者,如今已是古稀老人了,他们在哪里?
1986年8月7日上午 南京市卫巷28一7号
(七拐八拐地转了好几条小街小巷,才寻到这一排粉墙小台门。里面住着好几户人家。靠东边的这一家屋内拥挤,平房内还搭着阁楼。这是李秀英的家,她脸色腊黄,脸上有深深的皱纹和伤疤。她豁达开朗。她给我看日本兵留给她的创伤。身上有一道道刀痕,鼻梁上、嘴唇上有,大腿上、小肚子上的伤疤最大。她丈夫坐在旁边,他叫陆浩然,苍老的脸上有不少老年斑,白眉毛长长的,两眼白茫茫的。出生刚七天的小孙子正在喝糖水。)
李秀英(女) 69岁
我们原来在上海川沙,丈夫姓陆,是部队无线电报务员。我们是1937年3月结婚的。“八·一三”打仗了,我们一起回到南京,住在珠江路一个老乡家里。我怀着孕,当时十九岁。
我父亲是山东人,会武术,行意拳打得很好。我母亲死得早,我脾气坏,力气大,体质好,拳术能看懂,我丈夫打不过我。
日本人进城时,我躲在一个美国人办的小学校,就是现在五台山幼儿园那地方。丈夫跟着人撤退到了河南,他是一一八师参谋处的电报员。
梅奇牧师是大高个,瘦瘦的,会讲中国话,给我拍过照片。鼓楼医院医生叫我出院,我没地方住,他说,跟我去,住到珞珈路25号。那里有不少难民,全是教会的。我住了快半年。伍长德给我讲,他说梅会长给我拍的电影他见过,是在日本审判战犯时他见到的。
当时我父亲没事干,在汉中门给人管米行。我住在难民区小学地下室里,五六十个人,有男有女,两间房子大,我父亲也和我在一起。我父亲大个子,瘦瘦的,原在汉中门里稽查处当稽查员,山东郓城人,是李逵的后代。他是好好先生,不识字。日本人来了他在小学校外维持秩序。
18日,日本人来抓人,抓了好些男人去。我听说被鬼子抓去,女人要轮奸。笫二天上午刚吃过早饭,是稀饭。我随身带一个皮箱子,里面装衣物等。这时来了好几个日本兵,进来一人拉一个,说“走!”“出去!”地下室有两间,里面一个是女房间。我一看不好,连忙一头撞墙。我们有一二十个睡地铺,有一个窗,一半在地上。我撞在右上额头,一个大包。我剪短发,我昏过去了。
父亲来了,他喊啊叫啊。我醒了。当天下午,三个日本兵来了。我正躺在行军床上,父亲不在。一个日本兵来抓我了,有人说:“这是个病人!”这时,两个日本兵拉着两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出去了。
我穿着旗袍,红色的,蓝罩衣。那个日本兵朝我走过来了,他把其他人都赶出去,说:“姑娘……”就用手来解我衣服上的扣子。我一气,伸手去抓他的下面。他一弯腰,我就跳起来了,两个人打起来了。我一个鱼跃,刺刀抓到了我的手上,我朝他一捅,他伸手抓住了我的手,我就用头撞他,用牙咬他手。他大吼:“啊!啊!”
另外两个日本兵听到吼声赶来了。我连忙占领墙角,一手抓住日本兵的衣服。那时我劲大,豁出去了!赶来的两个日本兵拔出刺刀往我腿上刺来,我气!我没有知觉了,两条大腿上刺了好多刀,像刺在木头上一样。日本兵又朝我脸上刺来,耳朵下,鼻子,眼睛,嘴上,我一脸是血,我不像个人了,我玩命了!我把血往他们脸上吐。后来一个日本兵在我小肚子上刺了一刀,我穿着卫生裤和棉袄。我倒下了!
日本兵走了。别人把我父亲叫来了。他见我全是血,喊了一阵没回声,以为我死了,就和另一个老难民到后面山上刨了一个坑,准备把我埋了。
我躺在木板上,风一吹,我气缓过来了。父亲“秀英、秀英”喊我,我嘴里的血呼噜呼噜冒出来了。有人说“有气!”后来又找了一个人,把我抬到鼓楼医院。
一个美国医生给我缝的伤口。他说:“你一共有三十七刀!”
我住了七十多天医院,梅奇牧师给我拍照片。那时我头肿得斗大,头发都直了起来,像疯子。吃饭喝水从鼻子孔里流出来,上嘴唇破了,牙齿也掉了。现在全是假牙。
那时街道小,日本兵机枪架在十字路口,见人就杀。审判谷寿夫在军事法庭,桌上堆着许多人头骨头。去的人很多,有人作记录。
我现在有九个小孩,全家三十二个人了。老大是女儿,在五十四中教书,扬州师范大学毕业。老二女儿在南京电影机械厂当会计。老三在南京丝织厂。老四男孩,在清江棉纺厂当科员。老五也是男孩,在五一八厂劳资科。老六构件三厂工人。老七是采购员。老八在儿童福利院当保育员。小的在化工建设公司。五个男孩,四个女孩,有两个大学毕业的。靠政府救济,还有助学金。
1986年8月7日上午 竺桥31号
(他离我住的大院不远,从小营往南过珠江路,朝梅园新村去的方向走过竺桥,有一条整洁的小巷,丁字路口一间红砖的平房,门口有一台老式的缝纫机。他中等个子,花白头发,花白胡子,脸色红润,很健朗,戴一副老花镜,弓着腰,正在裁剪衣服。他讲一口南京话,“吓人啊!吓人啊!日本兵狠啊!”这句话他说了十多遍。)
刘永兴 74岁
我们是老南京了,住了好几代了。祖籍是安徽旌德。日本兵打进南京了,我们就躲到难民区去。走到新街口,一个炸弹炸了!我们逃到大方巷华侨招待所,我们弟兄、父母和老婆五个人一起住一间屋。
16日下午,一个鬼子走到我们住的门口,向我招招手说:“出来!”我出去了,他要我弟弟也一起走。到对面一个广场上集合。
后来叫排队,八个人一排,三排,穿黑衣服的国民党警察带队,后面日本马队押阵。路上尸体很多,男的女的都有,女的脱得光光的。国民党的官兵抓住后,用铁丝穿大腿。在挹江门里一串一串的,都穿着军装。
翻译官说话了:“做苦力去,到下关码头搬东西去!”有的人不去,当场一枪。
到下关的时侯,天擦黑了。沿路上,擦皮鞋的、买东西的,日本兵都带走。有人逃跑,一枪打过去。二十个人一捆,推倒就用枪扫。子弹从我肩膀上穿过,我穿着棉袍子,里面的棉花都打出来了。我在前面,就连忙跳江。有的人子弹打破了头,打断了手,又是叫又是哭。
我身子泡在江中,头露在上面。江边是烂泥,日本人没下来。他们枪上有刺刀,扫过后一个个用刺刀刺,刺过再烧。我心里难过,想可能要死了。机枪扫得我耳朵都聋了。
天亮了,日本兵走了,我慢慢爬上来,躲到一个防空洞里。躲了一天,晚上我转来转去,转到一个尼姑庵里。旁边有个草棚,里面有一个农民,四十多岁,我给了他十二块大洋,想弄点水洗洗,换一身衣服。农民说我是逃兵。我连忙说好话,后来他烧了一点胡萝卜给我吃,又换了一套对襟的蓝布老棉袄给我穿,弄一块手巾扎在头上。
到了晚上,对过楼房里一个鬼子看到我在吃东西就过来了,来了两个日本人,说“过来,你的,苦力苦力!”农民说:“去,我明天来看你。”
进去了以后,他们在烤火。日本兵用棍子在地上写:干什么的?
我用手指指衣服,说:做衣服的。日本人说:顶好!顶好!
他们还说我是中国美男子。那时我结婚才四个月,我哪有心思听他们“夸”我!我想家人,想得眼圈发黑,眼睛上火。后来眼睛好了,就给他们补衣服和做饭,抬来棺材当柴火烧。他们一个班,十二个人。
下关住了一夜,就到江宁镇去了,是走路去的。
在江宁,还抓了一个女的。是个二十多岁的农民,下午四点多抓来的。她穿着大襟衣裳,她吓呆了。日本兵叫我给她讲,叫她洗衣服。她说,快洗快洗,洗完我就走。我说,你走不了啦!鬼子把她带到后面房子去了,我早上起来没有看见她了。
当时住在江宁镇靠桥的一边,我干了四十二天的苦力。袖子上有“从军证”三个字的标记,上面有一个大红印章。我给他们挑水烧饭洗衣服。还有一个老头,没有劲的,还要我照顾他。日本人自己吃不了的才给我吃。后来他们要开到丹阳去了,所以把我放了。回来在宪兵司令部住了一夜,和鬼子一起来的。
回来后家里东西都被抢光了。我和弟弟以前是做裁缝的,很发达。现在四台机器都没有了,好多布也没有了。只好摆摊卖香烟过日子。
我记得中山码头那天夜里爬上来的有十多个人。
我金陵饭店去了好多次,我讲,日本人听了都哭。有四个访问代表团,他们送了我好多名片,有本多胜一、石岛纪之、君岛和彦,另外我记不得了。

徐志耕(右一)与李秀英(右二)和当年救护她的护士沈女士(右三)、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在一起
1986年8月7日下午 长乐路小心桥东街67号
(这里是城南的小街小巷,进入砖墙砌成的门,又拐了好几个弯,才找到砖头铺地的西厢房。一帘花布挂在窗前。他双眼炯炯,清癯瘦长,室内飘着茶香,他正在写娟秀的毛笔字。)
融通法师 66岁
我十六岁那年出家,先在古林寺上初级佛教学校,师父叫果言。后在城隍庙当和尚。那年“八·一三”上海打仗了,8月15号日本飞机轰炸南京。捷克式高射炮打起来像敲铜锣,打上去一团烟,晚上像一个火球,就是打不着。日本飞机飞得也慢。有一天来了一架大飞机,两架小飞机,哪里人多往哪里甩炸弹,太平路甩得最多。日本飞机来了会拉警报,几长几短。
我不喜欢躲防空洞,我在树下看。汉奸放红红绿绿的信号弹指示目标。保安队抓汉奸。南京有三个大队,九个中队。放信号弹的人太多了,没得办法抓。后来搞灯火管制,全城一片漆黑。
那年我也参加训练,练了三个月。派军队来当教官,光做动作。有枪没得子弹,没有打靶,枪不会打。我们佛教徒穿黄衣服,有一百多人,有男有女,成立救护队,尼姑也学包扎,我们学抬担架,学了没有用。下关有伤兵,我们去帮过一点忙。也上课,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
现在晨光厂、三山街那些地方,放的信号弹最多,日本飞机就朝信号弹的地方乱扔炸弹。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日本人什么时侯培养了这么多汉奸?他们怎么挂上钩的?就是他们开洋行雇的工人,一部分被收买了,成了汉奸。一个叫周国才的,住雨花门外打虎巷,他不识字,编鸡蛋箩筐的,他会讲日本话,是汉奸。日本人进城后,他吃得开了,跑前跑后。去肉摊买二斤肉,他要割五斤,他仗势欺人。
那时,许多没文化的人当了汉奸,有个剃头的也当了汉奸。不少有文化的人起来抗日。日军第一天进城,就有汉奸扛着旗子在石鼓路向莫愁路方向走,我在三岔路口看,白纸上面贴个红膏药,喊:“皇军进城了,大家欢迎啊!”这个人瘦瘦的,讲一口南京话。
还有个陶锡三,个子不高,胖胖的,当时五十岁样子。上海路难民区登记,我也去了,人很多。陶锡三先训一次话,讲:大家都要来登记,不登记抓到要杀头。国军官兵请出来,回家去发路费。不回家做工也行,当兵也行。
当兵的也苦,在南京没亲戚。他们认为中国人说话总算数,不会骗人的。陶锡三穿着大袍马褂,站在台上讲,台上放一张桌子。排队的人都用毛竹拦起来。出来的人就走到槽子里面去了。十六岁以上都可以去,有三四个人在登记,日本兵在旁边巡逻。不听指挥的,用毛竹片打。
登记证上有图章。登记后,就说:做工去!打仗去!就赶上卡车。日本人在队伍中检查,看手掌有否老茧,头上有没有帽印子。有的,推上车。不去,对不起。上车后,拉到城西清凉山,机枪架好,枪杀完了再来。又拉一车,去的人不闹也不叫。大家不知道的啊。后来知道了,过了五六天还不回来,知道回不来了,就不敢去了。后来良民证卖到一块银元一张。岁数大的和小孩,就不用登记放回家了。
我们城隍庙里当时住保安九中队。警察也被集中枪杀。虽然放下武器了,都被骗上汽车一批一批地杀掉,那个陶锡三就一批一批地讲。
南京当时有三百多寺庙,一千多僧人。香林寺、毗庐寺、古林寺都有当兵的躲到里面。12月16日,鬼子来了,就大喊:“皇军来了,都出去,集合!”一下找出来四十多个,出来后在大门口训话,站好。那天我在庙里念书,庙里有个二十多岁的小和尚生肺病,吃不下饭,人瘦得不得了,也要叫他出去集合。集合的人在山门外的菜园里,他爬不起来,走了一半路,就昏倒在草堆上了,枪响了。
山后还有人家,一个小孩跑过来找妈妈,鬼子看到了,一脚踢去,又一踩,头踩扁了!
现在市公安局原来是国民党伤兵医院。日本兵在医院里放火,里面的人哇哇叫。谁去救火就往里扔。一对老头老太挑一担木炭在走,突然一枪,老头被杀了。一个出来下河猫子(淘米)的女人,三十多岁,头上包一块布,被鬼子用刀刺死。是上午,在秣陵路口,地上有一滩血,一个老太坐在地上哭。我看见的。
明瓦廊有个春阳米行,日本人住在里面,我们城隍庙的一个伙计,叫刘怀仁,还有我舅舅,一共四个人,被鬼子抓去搬东西,从新街口到汉中门扛了两趟绍兴黄酒。刚把坛子放下,鬼子叫四个人跪下,一枪一个,把三个人打死了。我舅舅命大,鬼子子弹没有了,只好用刀砍。舅舅快五十的人了,头发白了,他四十八岁才结婚,找了个寡妇不到两年,可怜我外婆就这一个儿子。正要举刀砍时,一个军官出来,他叽里咕噜说了几句,不杀了。晚上又出发扛东西到中华门外,舅舅没有吃东西,走不动了,他看见路边有一个水塘,他会游泳,就一下跳进塘里去了。鬼子开枪,他扎下去了,他命大,逃出来了。这是他亲口给我讲的。
日本军队中有随军布教士,有一个叫小野獭大胜的和尚,就住在城隍庙,胡子长长的,中国话一流,三十多岁,个子不高,这人不干坏事,他念经,超度。有一个日本士兵跑到庙里来,手上拿着照片,结结巴巴地用中国话说:“老婆、小孩,死了死了的!”很悲伤的样子。
历史不容歪曲,历史要真实。告诉子孙,不能打仗。不是怕,是要有实力,那时我们四亿五千万人,日本只几千万人,为什么我们打不过他们?

徐志耕在日本当年生产细菌武器的地方采访
1986年8月8日上午 中山门外竹林新村15号
(沿着绿影婆娑的竹林小径向前走,面前是一片姜黄色墙壁的新村。我站在绿色纱门前,门口是绿叶艳红的美人蕉。出来迎我的是一位个子不高、花白头发、双眼红肿的老人,一边说话,一边不停地流泪。)
夏淑琴(女) 57岁
那时我们住在武定门老虎头新路口5号。一个大门,里面是平房,住两户人家。房东姓哈,是回民,三十多岁。他们家也两个女孩,和我差不多大。我家姐妹五个,我是老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还有外公外婆,父母是老南京人,父亲叫夏庭恩,高个子,长脸,他有文化,帮人家写写弄弄。母亲当时四十多岁。
日本人进城以前,老是跑飞机。我们睡在大桌子下,不能做饭,不能生火,吃炒米和锅巴,害怕日本飞机丢炸弹。舅舅、舅母的娘家人说:“你们还不走?”舅舅他们走了。我们不走。
日本兵进来是上午,我们正淘米洗菜,饭还没烧。外面死命地敲门,我父亲去开门。大门很厚,踢不开。我们很害怕。一开门,鬼子叭的一枪,把我父亲打死了。房东在后院,什么也不问,第二个打死了回民。后来日本兵又到我家,我跟外公外婆躲在房间里,我、姐姐、妹妹四个人躲在床上帐子里面。鬼子进来后,用刺刀一划,从床上把我大姐二姐抓出来,大姐被拉到外面桌子上强奸,二姐在床上活活被糟蹋死。外公外婆过来救,一枪一个打死了!
日本兵站满了一屋子,我吓得叫,日本兵用刺刀戳我,左肩、左腰、脊梁上刺了我三刀。第四个妹妹四岁,躲在被子里面,没戳到。
我醒过来后,一看,没有人了!二姐在床边上,大姐在桌子上,裤子一起脱光了。外公外婆在地上躺着。我爬出来,看见我妈在堂屋的桌子边躺着,没有裤子。还在吃奶的小妹妹被丢在院子里。
我和妹妹哭,我们睡在桌子底下。
房东的两个小孩也死了,一个女人在桌子下,都死了,到处是血,地上长的子弹壳好多。
家里有半缸水,我们用凳子站在上面,舀点冷水喝,抓一把炒米吃,夜里睡在桌子下。这样过了两个多星期。
死掉的两个姐姐上身有褂子,妈妈的奶子被割掉了,一个血人!外婆的一枪打在头上,脑浆溅了一地,白白的。
晚上我们把草填在地上,堂屋是砖头地。我找一条被子搂着妹妹睡。眼看半缸水快喝完了,后来有人来房东家拿东西就看见我们了。一个邻居路对面的徐奶奶进来了,我就喊她。她不敢看,往外跑,我跟着她。有日本人在门口。我看到对面卖杂货、糖果和香烟的小店烧了!
徐奶奶说,我看你家人死光了,你怎么回事还活着。她也怕。我说我们一天到晚睡在桌子下。
后来她来找衣服,我的衣服上血迹发硬了,像锅巴,就换上了大人的衣服。她带我们到老人堂去吃救济粥,后来舅舅把我们带出来了。见到舅舅时,他也哭死了。
死人都拖到一个大空地上,有好几百个,一大堆。我舅舅去找,找到外公外婆,我爸妈,埋到老虎头下,一大块空地全堆满了。我家门内十三个人死了十一个!
舅舅小个子,他哭得眼睛都红了。很多人哭、叫。有的全家死光了。我一想起来就哭,几十年了,忘不了,不会忘。我身上三个刀疤,是日本人戳的!
现在我家有十个人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三个孙子外孙,这是共产党给我的幸福。
日本人来以前,生活不是很好,小孩多,一个接一个。那时大姐已订婚给人家,妈妈舍不得她走,说:还小,才16岁。大姐很漂亮,长长脸,白白的,高高的。二姐也不丑,那时她十二三岁。
我眼睛一直烂,哭的。有人说是死人的瘴气,一直看不清。
我家虽穷,但很和睦,不吵不闹。舅舅家,房东家都很好。一家人吃青菜汤、稀饭、干饭、玉米面。
徐奶奶脚小,巴巴头,卖馄饨的。她头发白了,瘦瘦的脸,个子不高。
小妹妹后来送到孤儿院了。去了一段时间孤儿院,送给乡下一个亲戚做童养媳。舅舅不忍心,又要回来。妹妹吓呆了,不哭不叫,就是喊“要妈妈”。我手指指说:“妈妈死了。”舅舅帮人家做绳子,他小孩多,有的死了。他后来做小生意、卖菜,半夜三更去,还卖芝麻糖。
日本人胡子好长,好怕!我吓得头蒙着被子睡在里面,刺刀从外面戳过来。姐姐吓得叫不出来。姐姐待我好。她穿蓝黑大褂,滾白边。那天天气好。
我1961年到中山陵园工作,种花种树管理桃园。我1979年退休,现在很好。
房东家是回民,男的开炒货店,卖牛肉。女的长得胖胖的,高高的。他们两个女孩比我小。他家住后面,我家住前面。

徐志耕(右)在日本作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
8月9日上午 小心桥东街67号
融通法师
1937年那年,我在古林寺初级佛学校读了不到一年,日本飞机来轰炸,我回上新河家里去了。一个多月后,就跟六十多岁的师父果言到城隍庙了。
日本人进城后还放火。站在城隍庙院子里,最多看到有十七处失火,没有人救。建康路、三山街、中华路、内桥那边都是。还刮大风,瑞丰和绸缎庄是南京的大布店,唯一卖绸子呢子的,在三山街那边,我看见烧了一夜,东西全烧了。
有一事要提,汉中门那里有一个大米库,米很多,饿不死的。古林寺住过国民党宪兵第二团团部,撤走时留下一部分人化装退下来的。
日本人信佛,明治维新以后,信神了,认为神高人一等,就产生了武士道。忠君,一切效忠天皇。栖霞山有一块石碑,那里有一件事,有个佛头记的故事,《栖霞山志》里有,可以找苠山院长。佛学院管图书的王煜明和总务处长孟利群也可以找他们,电话是61706。
日本人进城后,国军部队有些逃进了栖霞寺。日本兵也追过来。到寺里发现一块石碑,碑上刻有“佛头记”。上面记录日本大地震以前民国初年的一件事,一个日本商人来到栖霞山千佛岩,从别人手里收了一个佛头,偷偷带回日本供在家里。大地震时他家没有倒掉。这个商人梦中见到佛头说话,佛头说要回中国去。“我头在这里,身子在中国。我救了你,你要把我送回去”。商人就把佛头送回了栖霞山。寺里的僧人接待了他,把佛头供奉后按原样修复好。日本商人为了报答佛头的恩情,又出资署名刻了“佛头记”的石碑。日本兵读了石碑,看到山门上有“寺庙重地,不准入内”八个大字,便下令不准进庙。这样,栖霞寺躲了不少难民,也保护了几百个官兵。部队后来化装过江走了,是从石埠桥到六合用划子过江的。抗战胜利后,躲避的军人又刻了一块石碑,将当年经过刻在碑上。两块石碑立在佛学院门口,一边一块,不知现在在不在?
所以栖霞寺名气很大,那时只要盖一个“栖霞古寺”的印章,南京到处能通行。
古林寺原来有五百多僧人。中华门外天界寺的老和尚被日本兵杀了。南京小的寺庙被烧掉不少。燕子矶的岩山有十二个洞。头台洞、二台洞、三台洞,还有观音阁,都为亡灵超度,跪在地上念经,念心经。阿弥陀佛!
日本兵进城,国军撤退,下关过不去,就沿江向东,到燕子矶,北面是长江,南边是陡山,只有中间一条路。对面来了日军,就打起来了。日军人少,我们有一百多人,背水一战,我们打败了日军。这时,日本的骑兵队来了,国民党军只好拼死过江,没有船,有的扶一块门板,死了不少。
新街口银行那时是日军的宪兵司令部。
城隍庙里我师父光辉也被日军踢伤。日本兵半夜来抢劫,要麻将牌、要大洋,没有,就打,就踢。师父被踢伤了,不能动了,我躲在楼上,是两个日本兵打的。一伤一吓,师父一年多后死了,1939 年春天死的。他是湖南湘乡人,当过北伐军,人和气,圆方脸,和毗庐寺和尚是老乡,死时不到六十岁,五十八九。
守南京的部队有四川、广东来的,有的新兵连手榴弹都不会扔。一队四川兵在中山陵打仗,松风阁上一个班被包围了,只有班长是老兵,新兵只会把手榴弹后盖拧开,交给班长扔。一个新兵逃到栖霞山,后来到城隍庙当伙计,只有十九、二十岁,个子不高,胖胖的,是刚补充进来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