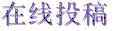2009年是我父亲韩述之(又名张钢)诞辰100周年,辞世10周年。父亲的一生充满传奇。
我父亲1909年出生于安徽省太湖县新仓镇一个破落地主家庭。我的祖父是个读书人,清末考秀才不中,经商又失败,家境逐渐衰落。幸赖祖母勤俭持家,勤于纺织,终于供养我父亲读完了大学,他1933年毕业于上海法学院。当时沈钧儒是上海法学院教务长;史良、沙千里等人是我父亲的校友。父亲毕业后,在上海给人家当了一年的家庭教师。第二年,经老师周新民(中共地下党员、后来民盟的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秘书长)推荐,以优异成绩被录入上海高等法院,开始从事司法工作。
从上海走向抗日根据地
那时抗日救亡运动日盛,而国民党消极抗日,压制救亡运动,加紧“围剿”陕北红军。在上海,社会矛盾极其尖锐。“昨夜一场大雪,今朝八百童尸”。父亲作为地检处工作人员,经常到验尸所视察,目睹许多大案要案的死者和冻死、饿死的受难群众,激起他的正义感和革命意识。他一边在地检处工作,一边参加中共领导的救亡运动,并主办《学习》半月刊,写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和罪恶。1940年他经顾准介绍,参加了共产党。
在旧上海,有公共租界(主要是英租界)和法租界,但租界内的司法名义上是中国人管。所以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沦陷,日本人却进不了租界。我父亲仍可以在上海法院供职。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原国民党的法院内迁。我父亲经党安排,于1942年8月进入新四军苏北根据地盐城。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是筹办江淮大学,任命他为筹备处秘书长。后来组织上要调一批干部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我父亲的要求被批准了。他就和从上海来的梅益、潘文静、王伟业、刘启林等人于1943年初随新四军二师的干部队,从二师师部驻地大柳郢出发,向延安进发了。他们经过鲁南到冀鲁豫根据地,过敌占区抵太行山,到达延安已经是1944年春天了。
后来我问父亲:“你到延安,路上走了一年多,感触最深的是什么?”他说:“有几件事终身难忘。一个是经过鲁南。鲁南是一个贫瘠的山区,可耕地很少,加上日寇的掠夺和自然灾害,农民生活艰苦,榆树叶子拌着粗粮吃。我们吃的都是发了霉的红薯粉做的窝窝头,这还是区公署照顾我们的。第二件是铁道游击队的护送。铁道游击队活跃在津浦路两侧:炸火车,截军火,夺棉衣,屡建奇功,打得日寇心惊肉跳。他们还负担起护送干部过路的任务。一个黑呼呼的晚上,他们领着我们过铁路,靠近津浦线时,敌人装甲车上探照灯向铁路两侧来回照射,我们紧贴地皮隐蔽。待装甲车开过,我们就靠近铁路东侧敌人挖的两人深、三米宽的深沟,用绳子把人放下沟底,在另一侧再把人拉上来。一部分人随后掩护,一部分人率领我们飞跑。此情此景,记忆犹新。”
从晋南走向延安
父亲在晋南一住三个月,住在农民家里。适逢农历春节,我父亲小组五人分到一只羊。父亲在上海开过小餐馆,会烧菜,就由他动手杀羊、剥皮、烧煮。由于长期不知肉味,他们五人把一只羊吃得精光,把肚子撑得几乎病倒。三个月后,他们接到通知:向西北移动,准备过同蒲线,有部队护送。有一天傍晚出发,走不多久下起了鹅毛大雪。在攀登一座高山时,气温急剧下降,雪花粘在眼睫毛上,好像长着白眉毛。当爬到两山之间风口时,气都喘不过来。后来才知道,这是太岳主峰之一的绵山,海拔1500米。天色越发昏暗,队伍必须在天黑之前找到村庄,否则可能冻死在山上。大家顺着陡峭的山壁,攀着灌木像猴子般地滑下去。下行几百米,终于找到山路,远远望到一个山村升起炊烟。他们在这只有七户人家的小山村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才同附近部队联系上了。这些事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向我讲的。
他们到达延安已是1944年4月,我父亲和王伟业、潘文铮、刘启林四人到中央组织部报到。父亲被分配在中央党校二部,参加了整风学习。当时正值党中央准备召开“七大”,全国各地代表云集延安。根据地的第一把手,经常到党校给他们讲课。“七大”召开后,党校就学习“七大”文件。特别是1945年8月13日,父亲还聆听了毛主席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一有历史意义的报告。父亲还参加了延安大生产运动。
重新潜回上海
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根据战略需要,从延安派遣大批干部到东北三省去。父亲也准备去东北。刚巧时任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的刘晓同志正在延安参加“七大”,刘晓向党中央建议:这些来自上海的干部还是回到上海对革命工作有利,得到中央批准。于是在刘晓率领下,他和一批上海同志潜返上海。党指示我父亲:法院是国民党统治的要害部门,你们要利用原有的工作条件和社会关系,再打进司法机关,隐蔽革命力量,和敌人斗争。父亲服从组织决定,放弃原想改行的打算。1946年1月,恰逢农历大年夜,回到上海,与留在上海的离别三年之久的我母亲见面,悲喜交加,可想而知。
根据党的指示,父亲必须找到公开职业。父亲找到上海高等法院院长、过去他的老上司郭云观求职,称自己从上海沦陷后,就返回安徽大别山的老家,教了数年小学,现在愿再投奔他的门下。郭云观是知名的学者,为人正直,学有专长,抗战前即任上海高等法院院长。上海沦陷后,拒不附逆,远遁乡下。抗战胜利后,复任原职。对我父亲的求职非常高兴,当即任命他为上海高等法院推事,后来还兼任书记官长(相当于办公室主任)。父亲利用这一合法身份,对旧上海的司法机关进行广泛的了解,掌握了不少机密。并根据党的积蓄力量、隐蔽斗争的指示,努力为党工作。1948年,同济大学遭到反动当局镇压,酿成血案。学生被捕多人,有些经伪法院判刑。父亲通过关系,千方百计保护学生,使这些学生无罪释放。1949年春,上海地下党成立市政接管委员会,父亲为召集人之一,负责整理伪市府所属机关的材料,为接管上海做好充分准备。
在人民司法岗位上的岁月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两个月后我父亲被任命为上海市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长,党组成员。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上海市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并兼任上海市军管会军法处长。1955年7月被任命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长,党组成员。他在担任上海市人民法院领导工作期间,坚持贯彻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严格按照法律办事,忠于事实,积极组织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运动、司法改革运动。他关心审判质量的提高和便民诉讼的程序,追求依法治国的目标;力主审判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反对抹煞历史和大呼隆的办案作风。1957年却受到批判。1958年整风反右补课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处理。直到1978年右派错划得到改正,重返司法岗位。组织上任命他为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直至五年后离休。离休后在身患癌症,视力下降的情况下,仍坚持写作,并主编出版了《司法日用手册》,还整理他自己办过的重大典型案例若干篇,1997年结集成为《审判实践与执法思维》一书,出版后成为法官学习参考材料。
父亲1999年6月11日在上海逝世。经上海市委批准,他的骨灰盒安放在上海革命烈士陵园(龙华公园)第五厅。
亲爱的父亲,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