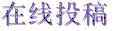2010年6月下旬,我应家乡江苏省江都市邀请,参加郭村保卫战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那一天,郭村的孩子们穿着新四军的灰布军装,在《保卫郭村》的音乐声中夹道欢迎当年参战的新四军老战士及其后代。
大姨妈夜送情报
我父亲吴仲邨1938年初参加革命,1939年春受组织委派第一个到郭村发展党员。郭村战斗时,父亲任新四军挺进纵队第一团特务连政治指导员。
随着参观的人群,我流连在郭村纪念馆一幅幅老照片前,这些老照片展现了陈毅、粟裕、叶飞、姬鹏飞、陶勇、惠浴宇、张藩、管文蔚、乔信明等新四军抗日将领和郭村军民抗战的丰功伟绩,这些老照片回放了郭村战斗的珍贵历史片断。在这些老照片中,我看到了和俞铭璜叔叔并排贴着的父亲的照片,也看到了大姨妈郑少仪的照片。
1940年6月27日晚,潜伏在“二李”(李明扬、李长江)部队第二纵队的政训员、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李欣(郑少仪)获悉敌方进攻时间提前至次日凌晨的紧急情报,她机智地甩掉身边“尾巴”,冒雨从泰州城奔跑数十里路,涉过七八条河流赶到郭村,在午夜12时前将李部进攻时间和兵力部署等情报送到叶飞司令员手中,为挺纵和郭村军民及时做好战斗准备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
28日拂晓,“二李”纠集13个团兵力对郭村四面包围,轮番进攻。坚守郭村的挺纵一团团长乔信明率部顽强抗击,击退李部多次进攻,撕开了包围郭村的缺口;郭村人民众志成城、踊跃支前;陶勇率苏皖支队及时赶到郭村增援;“二李”部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陈玉生、王澄宣布起义,加入郭村战斗,战局急转直下,李军全线溃退……
在一张张焕发着青春激情的老照片里,夜送情报的郑少仪照片,成为众多老照片的亮点,这是一张美丽娴静的青年女子倩影,在向着大家微笑着。我默默地说:大姨妈,我来看你了!
郑少仪原名李振芳,江苏扬州市人,出身平民家庭,兄弟姐妹6人。我母亲郑芬(李振芬)在家排行老四,17岁就跟大姨妈参加新四军。她生前常对我说,你大姨妈是家里长女,从小就懂事,读书非常刻苦,成绩一直优秀。她从小就喜爱武术,当年扬州著名的武林高手刘殿壁大师看她聪慧能吃苦,就主动收她为徒,免费教授武艺,她后来获得扬州市中小学武术比赛冠军。
小时候,常听母亲和家族亲友们谈起大姨妈战争年代的种种传奇:她性格刚烈,意志坚强,文武双全,会骑马,掌双枪。她两度潜伏敌营,凭着机智和勇敢,多次化险为夷,死里逃生。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大姨妈就是一个女英雄。
第一次见到大姨妈是1959年。那时我父母亲在苏州工作,大姨妈癌症手术后到苏州休养,我和母亲去招待所看她。“啊啊,晓鸣长这么大了,小时候我抱过你哪!”大姨妈瘦高精干,身着一件黑色绣红花毛衣,透出几分女性的雅致和妩媚。她操着带扬州口音的普通话,一把将我拉到怀里,笑着对我说:“姨妈姨妈赛过亲妈,晓鸣也是我的女儿呀!”那笑声和眼神驱散了初次见面的陌生和不安,我倒觉得她一点没有我想像中女英雄的威严。
1962年郭村战斗拍成电影《东进序曲》。那时我正读高中,开始关注和收集有关新四军的资料。我真后悔,那年暑假竟忘了让大姨妈给我讲讲郭村战斗夜送情报的故事,那是多好的第一手资料啊。
1966年“文革”爆发,江青首先下令要砸烂“公检法”,一时间,中央和地方政法机关首当其冲。大姨妈时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院长吴仲廉是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夫人,运动初期就被迫害致死,大姨妈成了运动的重点人物。她被游街示众、关押、揪斗、殴打,受尽侮辱和折磨。
1971年大姨妈获得解放,那时我父母也解放了,便接大姨妈到南京休养。我从武进县农村回宁,劫后余生的重逢,我们相拥而泣。大姨妈拍着我的肩说,都过来了,我很好的,很好的。她穿着宽松简朴的衬衣,更显瘦弱,唯有那双大眼睛仍闪烁着乐观和自信。之后我随父母陪她去泰州战地重游。
在郭村战斗前夕夜送情报的事发生后,国民党发出通缉令,悬赏捉拿她:“捉住小李欣,剥她皮抽她筋”。为此,我的外祖父遭到迫害,两次被日军抓捕,逼他交出女儿。经多次辗转,外祖父母带着小舅舅振谷全家逃往新四军苏北根据地。
大姨妈后来改名郑少仪,参加了江都、高邮、宝应一带开辟根据地的斗争。1946年她随新四军主力北撤到山东,后随大军参加渡江战役,南下浙江。
2002年10月,大姨妈离世,我们泣不成声的子女们怀着敬爱之情,送走心中永远的英雄!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三叔——花季少年英雄血
步出郭村纪念馆,迎面就是郭村战斗革命烈士纪念碑。我仰望纪念碑,耳边仿佛响起郭村鏖战的枪炮声和厮杀声,年轻的新四军指战员们,500多条鲜活的生命倒在了郭村的土地上。一位16岁的花季少年,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郭村战斗,但保卫郭村战斗的胜利有他一份功劳,他就是我的三叔、新四军烈士吴飞。
三叔原名吴叔邨,他兄弟三人,大伯精干,父亲内向,三叔活泼开朗,三兄弟参加革命的故事在吴家桥地区闻名乡里。
1939年初,新四军挺进纵队渡江到吴家桥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我祖父母积极支持抗日,慷慨解囊,捐钱捐粮,家里还接待了无数过往的新四军干部及家属,他们在父亲的家里养伤、养病、歇息,得到了细心周到的照料。这其中就包括接待过陈毅、叶飞、姬鹏飞、惠浴宇、乔信明等新四军领将。我三叔从小耳濡目染,小小年纪就要跟我父亲参加革命,要打鬼子救中国。1939年春天,中共苏北工委委员俞铭璜,中共江都县工委书记陈扬住在我家里,三叔与他们相处多日,关系密切,又一次提出入伍要求,父亲终于同意他的请求,就由俞、陈两人介绍,到新四军挺纵教导队学习。三叔改名吴飞,那年他刚满15岁。
1940年5月16日,新四军挺纵主力部队自皖东半塔集战斗胜利后东返吴家桥新四军驻地。挺纵一团奉命走扬州南线经过新老洲出江北,中途要连续渡过几道夹江。三叔和陆辉等战友们接到命令,急赴新老洲头桥,动员老百姓家家做大饼干粮,保障过江部队供给;组织大刀队对日伪据点严密警戒巡查;迅速将分散隐蔽在芦苇荡里的船只集中待命。天黑后,三叔和战友们赶到了施家桥,满载部队的大船进港了,队伍集合时,三叔向一团参谋长廖政国报告:“首长,我是挺纵派往新老洲接应的吴飞,现在前来为部队带路,头桥那边过江船只也都全部备好!”漆黑的夜,三叔带着部队,在曲里拐弯的田埂上急行,在午夜十二点之前提前到达头桥东边江边。队伍一到,立即安排上船。三叔和陆辉在江边笑着说:“放心吧,那边大刀队还在为你们放哨呢!”
1940年7月4日,郭村保卫战胜利结束。7月7日夜,粟裕将军率领江南指挥部及老二团、新六团要渡江北上,到吴家桥与挺纵、苏皖支队会合,整编后准备东进。2000多人的部队将乘船从新老洲头桥镇南边渡过夹江,经中闸奔吴家桥。我的三叔和三位战友受挺纵委派到江边组织接应。当最后一船部队安全渡过夹江时,天刚刚拂晓。随后,镇江、扬州两地日伪军获得新四军江南主力从新老洲渡江的情报,便出动3000多日伪军,从水陆两路包围了新老洲。我的三叔因多日劳累发起高烧打摆子,未来及撤离,他藏在新老洲东滩鄂家大棚一户老百姓家中。那天,区政府通信员胡奎叛变,领着日军挨家挨户搜捕新四军、共产党。该户老人让女儿坐在我三叔的床头,假装是他家生病的女婿,想掩护他脱险。可叛徒胡奎指认了我的三叔,他被逮捕了。不久,三叔又见到同行的三位战友因未及时转移也被逮捕,三叔悄悄对他们说,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我承认是新四军、共产党,你们的身份未暴露,不要承认。当日本鬼子拷问他时,三叔大义凛然,毫无惧色地说,我就是新四军!我就是共产党!他们仨都是老百姓,把他们放了,有话问我好了。三位战友安全脱险。三叔平静地对日军说,我不知道有什么任务,我也没有执行什么任务。日军气急败坏用皮鞭一次次地抽打,逼他招供。三叔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
灭绝人性的日军,竟将我的三叔双腿用铁丝扣在马的后面,拖着往前跑,殷红的鲜血一路流淌。三叔一路高呼,新四军万岁!共产党万岁!日军将我三叔拖到南老洲孟家港江边渡口,用烧红的铁丝穿过他的双肩,再用石头捆在他的身上,把他扔进了大江……
1940年7月7日,三叔刚完成任务,身体不适在家休息。他接到挺纵司令部命令,要接应粟裕部队过江,就立即脱下军装、换上便衣,未来得及同母亲说说话,就匆匆离家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三叔牺牲后,父亲将大伯的长女改名为继飞,意为永远继承三叔的革命遗志。建国初期,当地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历史的灵魂是真实
父亲家是吴家桥地区的名门望族,他的曾祖辈兄弟6人,前清时全部是举人,皇上赐封的一把大刀,被几代人珍藏在家里。抗战爆发后,父亲从省立界首乡村师范学校失学回家,为了抗日救国,放弃优裕生活,毅然参加了革命,在新四军里做民运和敌工工作。在父亲影响下,全家人直至长工、女佣都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到日军据点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传信、送信、接人送人,俨然成了新四军的地下交通站。
“文革”期间,我的祖父被定为“反动地富分子”遭到批斗殴打。那时,我父亲已失去了自由,身不由己,大伯也被靠边审查。祖父天真地以为自己的小儿子为国捐躯,是革命烈士,会躲过劫难,谁知他被告知,“烈士”是假的!老人不久气绝身亡。之后,我的大伯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全家押送原籍农村吴家桥劳动改造。大伯“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说来实在荒谬。抗战时期,父亲家里接待任务日益繁重,家庭开支日趋增大,大伯是长子,为了维持接待任务所需的财力,去镇江、南京和上海等地做些生意,填补接待透支,同时给新四军买些药品和生活用品,有时也跑跑交通、递送情报、接送人员。新四军有关部门给大伯仿制了一张国民党中统的“红派司”(工作证)作为沿途“通行证”,这张“通行证”使大伯顺利通过层层封锁线,行走于沦陷区与根据地。也正是这张“通行证”改变他后来的人生命运,甚至几乎要了他的命。
“文革”后期,父亲身患重病,自知不久于人世,他对三叔的事,一直放心不下,躺在病床上,郁闷寡欢。他说:“我最对不起的是吴飞,他从小跟着我参加革命,后来牺牲了,这么些年,也没有给他一个交待,没有把他的事情办好,我有愧啊,我对不住他!”那天,我守护在父亲床前,房门被轻轻打开,一个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人站在门前,啊,是大伯!在那个极“左”年代,父亲与大伯已断绝关系多年了。“我……我把老三……老三的证拿来了。”大伯声音哽咽,结结巴巴抽泣着。父亲接过去,凝视着,长叹一声,泪水顺着脸颊慢慢流下,父亲将它递给了我。“烈属证”三个字赫然呈现眼前。我泪如泉涌,捧在手里久久不放……
1997年清明,我回家乡为父亲扫墓,在新建的江都市革命烈士陵园纪念馆里看见了三叔的烈士画像。他身着新四军军装,年轻英俊、不苟言笑。这一年离三叔牺牲已过去了整整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