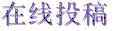1929年初,在我出生几个月时,父亲就受中共中央的派遣到广西开展革命工作,领导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建立右江革命根据地。之后,又率领部队冲破敌人的重重围堵,转战千里达到中央苏区,参加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

张云逸夫妇
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我们没有父亲的音讯,全靠母亲在广州当理发工人的微薄收入和一些亲戚的接济艰难度日。直到1937年中,父亲受中共中央的派遣从延安到香港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时,才通过组织找到我们母子,并把我们从广州接到香港,住在九龙荔枝角道。我9岁才第一次见到父亲,但父亲忙于工作,一直奔波在港、桂、粤、闽等地。就是在港的短暂时间里也是到处进行联系,工作十分繁忙。我和父亲见面的时间是很少的。还没等我熟悉父亲,他又于年末离开香港,参加组建新四军的工作。
父亲走后,我们住在九龙大南街。
1939年7月,组织上让我们随叶辅平(叶挺军长的弟弟,时任新四军军需处处长)去新四军。叶辅平是奉命到香港接收南洋爱国华侨捐赠的两车药品和军需物资,并把这些物资运往新四军。我们一起乘船从香港到越南海防。此时因物资未到,叶辅平留在海防等待。我们母子和几位要投奔新四军的女青年先行离开海防乘火车到河内,然后到镇南关(现广西友谊关)。在那里有两位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接待我们。他们用车送我们到桂林,叶挺军长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接见了我们。
后来听说,叶辅平跟车到广西,由凭祥到南宁途中,山路崎岖,道路艰险,开车的司机是南洋华侨,不熟悉山路驾驶,两辆车都翻入山下,叶辅平当场牺牲,车上的其他同志都不同程度地受伤。而我们几个先行的同志,免遭了这次劫难。
离开桂林后,我们经湖南入江西再到安徽新四军军部。在湖南境内,国民党得知我们要到新四军去,就百般刁难。有一次竟盘查了两个多小时,险些被扣留。到上饶稍事休息,便出发前往安徽。在屯溪附近的太平乘竹筏到达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
我父亲张云逸此时已在江北指挥部工作。军部安排母亲和我到教导队学习,给我们发了军装,我享受战士待遇,每月一元五角生活费。在教导队这个革命大熔炉里,我受到了革命教育,知道新四军就是过去的红军,是抗日打鬼子的革命队伍。我们平日就在村头山坡小松林的一小块平地上,坐在背包上听老师讲课。在这里还学唱了许许多多的革命歌曲:《新四军军歌》《大刀进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等。每一首歌都是一堂生动的政治课。我们小战士还参加过一次军部大会操,周子昆副参谋长亲自喊操,阵容壮观,个个精神抖擞。现在回想起来都难以想象自己一个十岁的孩子是怎样跟上大家的步伐的。1939年底,为了渡江北上去见爸爸,我和母亲离开了教导队。
由于日军对长江的严密封锁,我们几次渡江都因有日军巡逻没能成功,不得不在兵站等待时机。直到1940年2月,才随三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曾昭铭等干部战士25人成功过了江。渡江后到达无为县襄安附近,这里离我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驻地开城桥不太远,可以走陆路,也可以走水路。走陆路比较安全,不需要经过国民党的管辖区;走水路要经过国民党设在襄安附近的哨卡。当时因考虑到同志们经过一夜的渡江和行军比较困乏,就决定乘两艘小木船走水路前往,这样大家可以得到休息。
下午,当船行到襄安附近,遇到国民党保安第八团的一个哨卡。哨兵叫我们的船靠岸,要对我们进行检查。在国共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环境下,我们带有国民党军的正式护照,是合法通行。当时我们不了解国民党顽固派正执行反共政策,多次发生扣捕和杀害新四军官兵及家属的事件。我们认为只要给他们看一看证件就可以通行,所以就将船靠岸。开始只是两个哨兵对船进行检查,不一会儿,哨卡里的国民党兵大约有一个排出来占据了岸边工事,我们的小船就在其火力控制之中。曾副主任立刻派人到襄安进行交涉。记得是丁副官带两个同志一起去的。他手里拿着手榴弹,随去的同志也带有短枪,如果敌人动硬的就拼个同归于尽。我们在船上等了一段时间,回来的同志说,交涉的结果是不能放行,曾副主任决定亲自找他们的上级交涉。
我们随曾副主任离船到了襄安镇,这里是国民党保安第八团的驻地。我们进去以后他们就收缴了我们的武器,把我们25个人关押在一间大房子里。两天以后,保安八团派一个连把我们押送庐江广西军一七六师驻地。三个兵押着我们一个人,长长的队伍,走了一天还没有到,连夜赶路。夜里下起瓢泼大雨,伸手不见五指,队伍乱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派往军部领军饷的一位姓徐的干部,带着他从军部领来的3万元军饷,机警地逃脱了。事后听他说,返回部队途中,曾遇到土匪,但他巧妙脱身带着军饷回到部队。
在襄安,国民党只收缴了我们的武器,但到庐江以后,把我们携带的4万元军饷及私人物品都收缴了。我母亲的一个金戒指也被收走了。把干部、战士分开关押。曾副主任、丁副官、毛排长等几位排以上干部和我们母子关押在一起。此时同志们凭长期的斗争经历和对顽固派残酷性的了解,已经意识到敌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曾副主任,这位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老干部,估计到自己会遭到敌人的杀害,他想也许我们母子有可能出去,就将他身上的一支派克钢笔送给了我(此笔我一直珍藏着)。几天以后,敌人将我们母子押往桐城广西军一三八师驻地,单独关押在一间小房子里。从那以后就一直没有曾副主任和这些同志的音讯,估计是被国民党顽固派残害了。
被国民党关押后,母亲并没有承认自己是张云逸的妻子。我用了一个小学同学的名字叫“麦有就”。母亲和我都做好了死在国民党手里的准备。其实,国民党知道我们是张云逸的家属。在我们被保八团扣押之后,父亲很快就给国民政府林(森)主席、蒋(介石)委员长、桂林李(宗仁)司令官、白(崇喜)主任发了电报,电报中说:“窃职自参加辛亥革命以来,为国奔走已30年,遵先总理遗训,为国忘家,原籍仅存弱妻稚子,自给自食,苟延残喘,不意去岁粤中沧陷,逃难异乡,流离失所,幸获亲友协助,跋涉数千里,奔抵江南军部,近又冒险渡江来职部,路经安徽无为,竟被该地驻军保安第八团将职妻韩氏、儿远志及护送官兵20余人,与军饷法币7万元及一切物品均被扣留……请钧座电令安徽李主席,明令释放妻子与人员,归还所扣国币、枪支等……”在桐城,有一天他们把我们母子带到一个大厅里,押上一个犯人。他原是十九路军的将领,叫云应霖,是海南同乡,和我们认识。他可能是因主张抗日和我军的关系较好而被逮捕的。他指认我们就是张云逸的夫人和儿子。此时母亲觉得承认不承认反正都是死,也就承认了是张云逸的家属。这样就明确了我们是新四军抗日将领家属的身份。
此前,我们母子被关在一间民宅里。从小窗口可以看到其他的一些“犯人”。不久,他们又把我们关到另一处宅院的最里边的一间小房子内,由带枪的便衣看守。在被关押的几个月的时间里,曾将我们由桐城转押到岳西、霍山、六安等,最后交给国民党第十三游击纵队司令部看管。在这里允许我们到户外走动,看样子是准备放我们母子回新四军了。1940年9月,我方是由张翼翔团的兰翔营长带队伍来接我们的。交接是在一个夜晚。我们终于回到了自己的队伍里,我们自由了。真是悲喜交加,激动万分。
我们随兰营长的队伍前往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我们被国民党扣押7个月后,终于在路西太平集江北指挥部司令部驻地见到了父亲。从此我就在党的教导下,父母的关怀中,在备受同志们的爱护的革命大家庭里学习、工作、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