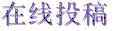抗日战争期间,我祖父的人头在日本鬼子那里值500大洋。祖母向我讲述祖父的时候,已经88岁,牙齿全部掉光,脸上的皱纹如核桃一般。
祖父是个神枪手
1942年,28岁的祖父就在一次抗击日本鬼子“清乡”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多少年以后,我曾四处寻访当年熟悉祖父的老人,试图了解祖父短暂而传奇的一生。老人们的描述,使祖父在我心里栩栩如生。
祖父当年住在南通城东十六里墩,是一个大姓家族。我查过族谱,最早是明代从江南句容来通州石港赴任的葛姓总兵,一个朝廷派来抗击倭寇的武将。至祖父一代,家道已渐衰落,但仍有良田几十亩,开有中药铺。祖父叫葛兰丰,兄弟5个,祖父是老三。在江北乡下,大家就叫他葛三侯。
曾祖父是个精于世故的商人。当年战事不断,他把大儿子送到了国民党那边做事,把三儿子送到了共产党的部队,两边都有人,便可左右逢源。其他三个儿子则送到隔江的上海,或读书、或经商。祖父在新四军的官职,我估计最多也就是连排长一级。但说到枪法,倒是首屈一指。
我的舅爷,这个当年新四军来时还光着屁股的男孩,说起姐夫三侯,至今仍两眼放光:三侯坐在树荫下喝酒,见天上有大雁飞过,只见他右手在腰上一拍便握枪在手,顺势往腿上一蹭,子弹上膛抬腕便打,整个过程也就眨眼的工夫。完了一拍舅爷的脑袋:“去捡回来,晌午炖上。”舅爷出去不一会便拎只大雁回来了。
祖父娶了村妇救会长
祖父的爱情诞生于五月豌豆花开的时节。新四军的队伍驻扎在掘港国清寺休整。遇见祖父那年,祖母才19岁,是村里的妇救会长,比祖父小七岁。祖母向我回忆这段美好时光时,掩着没了牙的嘴唇似乎还有点害羞。
祖父的部队隶属新四军一师三旅在苏中四分区的地方武装,我为此查过新四军在通如海启地区活动的史料。四分区曾根据粟裕的指示,组建短枪队在敌后开展游击和锄奸。据祖母讲,原先南通城也有国民党军队,驻扎在军山上。可是1938年日军坂冢旅团5000余人从姚港登陆后,这群军人溜得不知去向。只有祖父他们的新四军队伍长年战斗在敌占区,割电线,炸碉堡,打伏击。日本鬼子恨透了新四军,城里观音山的街上就有悬赏捉拿我祖父等人的布告。
1941年秋天的一个晚上,祖父趁着夜色回家看望父母。不料汉奸告密,日本鬼子偷偷进了村。夜深时分,村里狗乱叫,警觉的祖父拔枪吹灯翻窗而逃。索索发抖的曾祖父走投无路只好跳进粪坑躲藏,被恼羞成怒的鬼子抓起来残忍地割了头,剖了腹,然后一把火烧了我家的祖屋。曾祖父的头颅在观音山街口的旗杆上挂了半个月,后来还是中共地下组织通过在伪军的关系,花了15块银元赎回埋葬。
带领三兄弟参加新四军
杀父血仇,祖父肯定要报。汉奸绰号“李大鼻子”,曾在国民党军当排长,淞沪会战那年受伤逃回江北老家养伤,日本人来后当了汉奸,手上有好几条人命。“李大鼻子”狡猾警觉,杀他不是件容易的事。祖父怕单干不行,召回在上海的三个兄弟。枪不够,他们就趁黑夜去城里摸日本鬼子岗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李大鼻子”一家全死了。祖父带着三个兄弟连夜参加了新四军大部队。此后,祖父的头颅开始升值到500大洋。
1943年,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日寇开始了极其残酷的“清乡”。一个三伏天的早晨,祖父的队伍被包围了,歪脖子机枪在玉米地里突突突地叫着,密密麻麻的鬼子和伪军涌来。队伍已经被打散,祖父一路狂奔,胸口已经中了一弹。突然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祖父走投无路一头扎入河中,鬼子一阵机枪向河面扫去,祖父胸前被打穿两个窟窿。祖父的三个弟兄也在战斗中牺牲。
我陪祖母为祖父迁坟
祖父的追悼会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开得隆重而热烈。据祖母讲,新四军来了很多人,梁灵光司令派出的便衣警戒哨足足有几里地,一直派到了鬼子岗楼前。
祖父牺牲的时候,父亲才出生6个月。鬼子伪军天天进村叫嚣杀光抗日家属。村里是不能呆了,祖母抱着襁褓中的父亲在芦苇荡里四处逃难,最后决定逃往如东的海边去。在去如东的木船上,又冷又饿的祖母身上没有一个铜钱,父亲在祖母怀里蹬着小腿哭喊不已。艄公望着头戴白孝布、脚穿白孝鞋的娃娃,一问晓得是抗属的伢儿,不仅没要一文的船钱,反而从腰里掏出一大把铜钱给了祖母。
我见到祖父的时候,已经是45年后了。我15岁那年父亲去世,祖母决定把祖父的遗骨迁回海边小村,让他们父子团聚。来到祖父当年牺牲的地方,昔日的硝烟早已褪去,当年宽阔的大河如今成了奄奄一息的水沟,河滩已成了一片随风起伏的麦田。面对祖父的墓穴,祖母让我们跪下。那一刻,我看到祖母满是皱纹的脸上两滴浑浊的眼泪落下。我不知道祖母的日子在血泪里浸泡了多长,只是清楚的记得那个傍晚,熟透的小麦遍地金黄,晚风从麦田中吹过。天边,夕阳西下,残阳如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