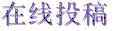聂绀弩
从上海到延安,一次遂愿之行
在上海北四川路与窦乐路交叉口,有一家标志醒目的“公啡”咖啡店,坐落在老上海公共租界边缘、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店主为挪威人,经营此店已有几十年历史。咖啡店为两层楼结构。楼上为西餐厅,临街是一排宽敞的落地玻璃窗,街市的热闹一览无余。
1936年9月的一天,在“公啡”咖啡店二楼,有两人相对而坐,私语窃窃。从他们并不轻松的神态中能感受到所涉内容的非同一般。其中一人是受中共中央派遣在上海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冯雪峰。另一位则是时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上海沪西区大组组长的聂绀弩。正是这次约见,冯雪峰交给聂绀弩一项特殊的任务:护送丁玲前往西安。
作为著名左翼作家的丁玲此前曾遭国民党特务的绑架和软禁,在冯雪峰等人的精心策划下,丁玲终于冲破藩篱,获得自由。根据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决定,丁玲将转道西安秘密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考虑到此行的安全,故选择了左联同仁聂绀弩同行保护。聂绀弩慨然应允,告别了已怀身孕的妻子,秘密离沪。
这次任务很特别,聂绀弩与丁玲以夫妻作掩护,一路有惊无险,安然抵达。在西安,他们见到了前来联络的潘汉年。聂绀弩完成任务,心殊释然。眼见丁玲将前往保安,聂绀弩突然意识到神往已久的中共中央所在地竟近在咫尺。他随即向潘汉年表达了亦想前往保安的愿望。但潘汉年还是要求他返回上海。因为上海地下工作需要他,而他的妻子仍在上海,一旦身份公开恐受连累。
聂绀弩只好折返。途经南京时忽闻鲁迅逝世噩耗,他立刻乘火车赶往上海。大师远行,山河失色。聂绀弩随即融入到万国殡仪馆的悲恸人群中,并与萧军、胡风、黄源、巴金等成为鲁迅出殡的抬棺者。以后,他曾以题为《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了》的新诗来讴歌鲁迅并寄托他的思念。
1937年8月13日,黄浦江畔的枪炮声揭开了淞沪战事的序幕。上海这座闻名于世的大都市经历了一场血与火的洗礼。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坚定的抗战信念、上海军民的同仇敌忾、谢晋元部坚守四行仓库以及女童子军杨惠敏泅水献旗等,浓缩了淞沪抗战的激情画面。作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员的聂绀弩很快便融入抗日救亡洪流中。但最终上海还是沦陷了。面对残酷现实,聂绀弩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一队前往武汉继续抗战宣传。同行中有马彦祥、贺绿汀、宋之的、塞克等。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是长江中游的一个重要城市。抵达武汉后的聂绀弩,强烈地感受到一种迥异于其他城市的地域激情和弥漫其间的抗战气息。演剧一队在武汉三镇进行街头宣传演出,以《放下你的鞭子》为代表作。一时观众如潮。聂绀弩没有演剧才能,唯有继续写作。当时胡风主办的《七月》杂志成为聂绀弩的重要阵地。不久,聂绀弩受命主编《新华日报》副刊《团结》。对于曾经主编过《动向》《海燕》杂志的他来说,这可谓专业对口,也驾轻就熟。但很快又有了变化。次年初,根据组织安排,聂绀弩与艾青、田间、萧军、萧红等前往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
令聂绀弩颇感意外的是,在临汾他居然见到了丁玲以及他的老乡也是他入党介绍人吴奚如。原来,丁玲、吴奚如正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在临汾演出。故人邂逅,不禁大喜过望。然而这种陶醉很快便被战火硝烟所淹没。其时,日军攻下娘子关后,正由晋北南下。临汾首当其冲。形势危急,聂绀弩以及一帮“教授”们即随丁玲、吴奚如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一道紧急撤往西安。
这时候的中共中央已经从保安迁往延安。来到西安的聂绀弩又一次感觉到与党中央所在地近在咫尺,一种强烈的地域魅力在吸引着他。在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聂绀弩见到了周恩来。他随即表达了欲往延安的想法。经周恩来同意与安排,聂绀弩如愿以偿地与丁玲等人一起抵达延安。
延安的地域风情和抗日军民的精神风貌犹如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仰望巍峨耸立的宝塔山,聂绀弩兴奋异常。这充满象征意义的地标式建筑,曾经让他的内心有过多次遐想与荡漾。他终于见到了神仰已久的毛泽东,那是在陕北公学的开学典礼上。第一印象是平易近人,随和幽默,有领袖风度,极富个人魅力。会后,在丁玲的介绍下,聂绀弩与毛泽东近距离地见面谈话。以后他曾回忆说:“和他谈话得来的印象与听讲的印象很统一。他不威胁人,不使人拘谨,不使人觉得自己渺小。他自己不矜持,也不谦虚,没有很多应酬话,却又并不冷淡。初次见面谈起来就像老朋友一样。”不久,毛泽东请聂绀弩、丁玲等一些新近来延安的文化人吃饭。聂绀弩与毛泽东有了更近距离的接触。在席间的轻松气氛中,聂绀弩谈了他的延安印象,并称“中国的希望就在这里”。
但聂绀弩对延安仅仅是做一次考察,也是一个过客。他并没有留伫延安的意思。这是因为他的心一直向往着抗战前线。
手持周恩来介绍信,前往皖南军部报到
聂绀弩带着对延安的记忆再次前往西安,希冀通过周恩来的介绍直接到抗战前线工作。
聂绀弩与周恩来可谓关系微妙。这倒不仅仅因为聂绀弩在黄埔二期时,与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有过接触。而是周恩来常常戏称聂绀弩为“妹夫”。这种指代蕴含着一层特殊的关系。
1919年,周恩来、邓颖超、周之濂、马骏等在天津发起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其中,邓颖超与周之濂是天津女师时代的同学和闺蜜,关系十分融洽。周之濂有胞妹周之芹年仅11岁,为“觉悟社”最小成员。邓颖超为此一直称周之芹为“阿妹”。后来,周之芹因仰慕邓颖超而改名为周颖。1929年,周颖成了聂绀弩的妻子。这样,周恩来戏称聂绀弩为“妹夫”,便有些顺理成章的味道了。

聂绀弩和周颖的结婚照(1929年摄于南京)
到达西安的聂绀弩未能见到周恩来。因为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已往武汉进行抗战的统一战线工作。聂绀弩随即赶往武汉。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汉口旧日租界,一幢四层楼建筑,原为一家日本洋行。它当时也是中共代表团驻地。当时驻八路军办事处的中共代表团与中共长江局已合二为一,只不过对外对内叫法有别。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聂绀弩见到了周恩来,同时还意外地再次见到了他的老乡、已担任周恩来秘书的吴奚如。面对周恩来,聂绀弩坦言相陈,追随而至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有机会到抗战前线去工作。
周恩来很高兴聂绀弩能有此要求。但聂绀弩毕竟属于文人,是否适合在前线工作还不清楚。较为了解聂绀弩的吴奚如于是向周恩来建议,让聂绀弩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周恩来知道叶挺、项英正在延揽各方面人才,觉得聂绀弩去那里也挺适合。聂绀弩的去向就这样定了。当周恩来告知聂绀弩决定后,聂绀弩欣然同意。
皖南新四军军部位于环境优美的泾县云岭镇罗里村。云岭东接泾云公路,南依青弋江,西靠黄山,北望长江,叠嶂染翠的起伏山峦,茂密葱绿的森林竹园,潺潺流水的沙石河道以及青砖黛瓦的徽派建筑,勾勒出独特的地域风貌和魅力。叶挺曾有“云中美人雾里山”之句来赞美这样的环境。
聂绀弩是手持周恩来介绍信来到新四军军部报到的,自然受到叶挺、项英的欢迎。叶挺、项英对新四军的文化建设非常重视,当时在军部已有很多文化人云集。聂绀弩意外遇见了以前结识的几个左翼文学的好朋友徐平羽、丘东平、彭柏山、黄源、赖少其等人。他们都在军部从事宣传和敌工工作。大家聚在一起谈诗论文,编辑创作,心情怡然。
皖南新四军军部对聂绀弩而言,是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他在这里接触了很多新四军战士,感受到他们身上那种朴实的作风和坚定的意志,以及一种积极昂扬的精神状态。皖南的环境,皖南的战士,皖南的氛围,让聂绀弩觉得一种无法自抑的创作激情呼之欲出。于是,便有了散文《巨像》《小号兵》与小说《山芋》等作品,以及《不死的枪》《收获的季节》等诗作由心而出。这些由皖南而生创作灵感的作品,分别发表在《七月》《抗敌》《文艺阵地》等报刊上。
散文《巨像》对皖南充满了浓烈的情感,那视野中的山影宿雾、丛竹溪流、田野村路,无不让他情有所寄,心有所往。“我曾经看见过疏林的落日,踏过良夜的月光;玩赏过春初的山花,秋后的枫色。绿杨妩媚,如青春少女;孤松傲岸,似百战英雄。高峰奇诡,平岭蕴藉,各各给人一种无言的启示。如果一个朋友,要交往越久,才相知越深,生死患难中,才有真实的情谊;自然的奥秘也应该不是浮慕浅尝,所可领会。那么,我对它们的低徊赞叹,岂不是为了我和它们有了较长的往还么?”
颂吟美好景致,是为了衬托出祖国大好河山被日军铁蹄践踏的严酷现实。
“祖国的大地整块整块地在魔手底下,铁蹄底下,喘息,呻吟,颤抖,挣扎,愤怒!强盗所到的地方,纵然也是春天吧,我不相信太阳仍旧是温暖的。”聂绀弩由此大声呐喊,呼唤抗战。他在皖南,在新四军中看到了希望。置身于抗战的队伍中,聂绀弩突然觉得过去的“小我”,已仿佛成为一尊“人类英雄的巨像”。而这一“巨像”恰恰是整个新四军以及抗日军队的群像写真。
散文《小号兵》也是以新四军战士为原型,写出小号兵的可爱以及号音的激昂嘹亮。“在他们的手上,号角闪着灿烂的金光,金光和酡颜又交织成黎明时的霞光万道,在这泥泞的街上,竟是不曾想到的奇美,招诱着寥落的行人。那些小号兵迈着坚实而齐一脚步,踏着泥浆,踏着尚未融解的积雪,污浊的泥浆向四面飞溅,泥水把他们的胶底鞋都浸透而且吞没了,他们毫无感觉,毫无顾恤似地,踏着号音的节拍前进”。
聂绀弩笔下那在泥泞中坚定前行的小号兵,是一种象征。那坚定中既有新四军的抗战英姿,也有聂绀弩的情感指向。
与《抗敌》相伴的日子,充满和谐与温馨
新四军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当时军部即有一报一刊,均以“抗敌”命名,分别为《抗敌报》和《抗敌》杂志。聂绀弩的抵达很快便有了用武之地。他被任命为军部文化委员会委员,负责《抗敌》杂志的编辑工作。聂绀弩前后共主编了三期《抗敌》。这为他的编辑生涯又增添了新的丰富内容。
《抗敌》的稿件十分丰富,虽然办刊条件很差,纸张缺乏,印刷粗劣,没有稿酬,但是上至军长叶挺、支队司令员陈毅,下至基层连排普通战士,都是《抗敌》的热情作者、读者和义务通讯员,《抗敌》真正成为了官兵们离不开的刊物,大家都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它。

《抗敌报》
考虑到军部一报一刊已经发表了不少文艺作品,军政治部于是决定成立一个“抗敌丛书编委会”,累集这些作品,同时再组一部分新稿,出版一套抗敌丛书。筹组工作由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副团长徐平羽负责。聂绀弩自然是首选。他也成了由四人组成的编委会的负责人。其他成员分别为著名诗人辛劳以及从民运队抽来的文学青年罗涵之(菡子)、林琳(林果)。
编委会设在一家老乡的小屋里。小屋既是办公室也是宿舍。进门右首的窗下,刚好放下一张长条桌,是辛劳写作的地方。正中一张八仙桌,聂绀弩、林果、菡子各占一方。靠后边是用木板搭架的简易床,聂绀弩与辛劳即睡于此。
编委会是一个特别有趣与和谐的组合。聂绀弩和辛劳是著名作家、诗人,菡子与林果当时只是有着文学梦的女青年。在菡子和林果眼中,聂绀弩与辛劳是师长辈的,一起共事,不免拘谨。特别是他们对聂绀弩并不熟悉。但这种拘谨很快便荡然无存。
当时编丛书的书稿不够,编委会便需自己创作。还不会写作的菡子不知如何下手,聂绀弩就告知她“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自已熟悉的事情。你不是做民运工作的么?那就写在民运工作中遇到的人和事好了。” 在聂绀弩的鼓励下,菡子开始了创作。第一篇作品完成后,腼腆的她将稿子放在聂绀弩的桌子面前就跑出去了。因为心里没底,她竟在外面躲了一天。在得到聂绀弩的肯定后,菡子无比地兴奋。于是第二篇、第三篇陆续完稿,中篇、短篇、散文一泻而下。
以后成为著名作家的菡子每每回忆这段时光,总是对聂绀弩充满敬意和感激之情。她说:“他似乎从未向我们交待什么任务,就是叫我们写,写了以后,他都看得仔细,意见也提得切中要害。有一次林果给他看一篇稿子,他边看边问:‘是紫色的山峦么?’林果不加思索理直气壮地指着窗外的远山说:‘你看!不是紫色的山峦么?’老聂翻了翻眼睛,正视着林果说:‘现在是冬天,你写的不是夏天么?’林果恍然,羞愧地说:‘对!应该是青色的。’老聂又指着一处说,‘金色的稻穗是不错的,可你写的是夜行军,怎么看得见金色呢?只能闻见稻香味嘛。’他对我们的批评和鼓励,都使人心服口服。当我们写出好的作品,他还推荐到外面去发表。”
为了帮助年轻人提高文学修养,聂绀弩常到军部图书馆去借《罗亭》《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等世界名著给她们读。菡子说:“在他指导下的写和读,对我们一生都起着作用。”
聂绀弩的文人风格和个性也给编委会同仁留下深刻印象。若干年后,菡子的回忆还是那么充满细节:“老聂受不了任何约束。当时军部很强调军容风纪,可老聂最怕打绑腿,也很少戴军帽,头发七横八竖从未认真梳理过,一件棉大衣总是挂在肩膀上。走起路来,瘦长的个子一摇一晃,脚步不紧不慢,一股悠闲劲儿。但他头脑敏捷,语言锋利,对事对人常常一针见血,有时又很诙谐,令人捧腹大笑,而他却还一本正经。”
聂绀弩落拓不羁,真挚坦率,从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好恶。再加上他的自由放任,在一些人眼中,难以看到他的长处,认为他狂妄不近情理,生活散漫,旧文人气习严重。而常到编委会的徐平羽却理解他、信任他、尊重和钦慕他的才华。他称“老聂是有黄金般头脑的人,还有一枝犀利的笔。”徐平羽知道聂绀弩的性格,尽可能给他力所能及的照顾,比如特许他不出早操,津贴费可以提前支取,发津贴时还常约聂绀弩到云岭街上的小餐馆里打牙祭。徐平羽是到编委会次数最多的人,他与聂绀弩是左联时期的老相识。聂绀弩平时话不多,但每次徐平羽到来后,两人便谈笑风生,滔滔不绝。后来知道,徐平羽常到编委会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给聂绀弩以友情的慰藉。菡子说:“在我们这个小集体里,当我们逐渐和他熟起来的时候,我们觉得他是平易的,是可敬可亲的。”
编委会的小屋在皖南军部还是小有名气的,来客不在少数。年轻的女孩子们是来找菡子和林果的,同时亦想看看作家和诗人。年纪大些的多半是文人,那是聂绀弩和辛劳的朋友。有作家丘东平、彭冰山、黄源、吴强等人,他们大都在军政治部工作,只有丘东平是做敌工工作的,但他却是颇负盛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每每作家云集,小屋气氛顿显活跃、热闹。他们天南海北,论古道今,有时也会慷慨激昂地激烈争辩。而多数的话题是围绕着文学的,谈作品、谈作家、谈书中描述的人物,谈书的思想内容。小屋弥漫着浓郁的文学气氛。
1939年2月底,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巡视和传达中央指示。聂绀弩与编委会成员都在陈家祠堂听了周恩来的报告。不久听说周恩来即将离开,大家都有些茫然若失的感觉。于是,聂绀弩与大家商议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背景,创作独幕话剧《圣诞节之夜》,献给周恩来。聂绀弩与大家各自分工,挑灯夜干,经过一夜的的集体创作终于脱稿。第二天清晨,菡子、林果小心地将剧本订好,在雪白的封面上扎上一根美丽的缎带。聂绀弩磨墨执笔,在封面上书写了剧名。最后由徐平羽亲自把剧本送到周恩来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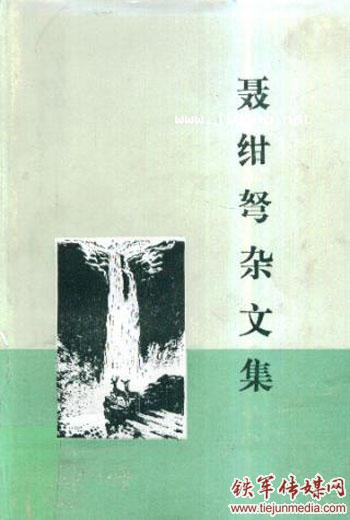
与陈毅一见如故,从诗友到“红娘”
聂绀弩虽然已成为新四军中的一员,但距离他向往的前线还有一步之遥。他在等待这样的机会。
在得知常来看望的徐平羽将调往前线工作,聂绀弩不禁有些失落,毕竟知音难求,很难再有那样激情畅叙的机会了。徐平羽行前特地邀请聂绀弩一同前往茅山根据地看看,并告诉他好友丘东平已被任命为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的秘书,亦将同行。这样,聂绀弩便随同他们一起前往茅山。
1938年6月,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率部开赴江南进行敌后抗战,创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茅山山势秀丽、林木葱郁、峰峦叠嶂、千姿百态。主峰大茅峰,似绿色苍龙之首,也是茅山的最高峰,海拔近四百米,虽不算高,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自从新四军一支队开辟茅山根据地后,这里就成了一片遐迩闻名的抗日热土。
陈毅本身即为儒将,对文化人十分尊重。徐平羽、丘东平来一支队工作即为陈毅所提议。看到他们报到,陈毅自然很高兴。他甚至对丘东平说:“我们需要千百万个作家和记者来部队观察体验,尽快写出伟大的作品来。你是最先来新四军的作家,我由衷地希望你能多写快写。不过,目前还必须协助我做些对外工作,因此有必要在你这个大作家的头衔上加上兼职两个字。”陈毅与文化人的亲近由此可见。而聂绀弩的到来完全是他即兴所为,出乎陈毅预料。当然也给陈毅一个惊喜。
陈毅极善写诗,尤其是格律诗,戎马生涯中常吟诗作画,是杜甫、辛弃疾、陆游的坚定“粉丝”。他身边经常会有几本诗词类书,战争间隙开卷吟诵,心有慰藉。作为诗人的陈毅对聂绀弩早有所闻,茅山意外相见,甚感快慰。聂绀弩与陈毅可谓一见如故,诗词成了他门之间最好的媒介。他们常秉烛夜谈,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他们探求意境,切磋格律,相互唱和,抒发胸臆。陈毅的旧体诗词创作,本来就可圈可点,如《赣南游击词》《梅岭三章》等。这些诗作莫不体现出陈毅革命家的伟大情怀,也是他早年风雨漂泊的革命生涯的真实记载和情感素描。
陈毅视聂绀弩亦师亦友,感觉他们间的精神世界完全契合,都具有诗人的放达和率真的气质。陈毅常将自己的旧作拿出来让聂绀弩评点。聂绀弩直率的脾气也很对陈司令员的胃口。在支队司令部里,经常可以听到陈毅的大嗓门:“对头!对头!”那是陈毅高兴得意时的口头禅。
在不长时间的接触中,聂绀弩对陈毅非常敬佩,评价极高。他认为陈毅能文能武,是难得的一位儒将。而且陈毅从来不摆架子,生活极为简朴,待人和蔼可亲,讲话幽默,乐观自信。陈毅爽朗的笑声极富个性魅力和感染力。聂绀弩觉得来茅山最大的收获即是结识了司令员陈毅。
不知不觉聂绀弩抵茅山已十多天,他要考虑回军部了。陈毅很想留聂绀弩在一支队,但他知道像聂绀弩这样的文人并不适合在前线,甚至在部队的生活他都有可能不适应。于是陈毅对聂绀弩说:“我看你是一位人才。如果我们打下一个县城,或者一所大学,你去当个县长或者校长什么的,你行!但现在是战争时期,又是神出鬼没的游击环境,行军打仗,一天走百几十里,你不行!你在这儿,我看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你要是想走就可以走,不要不好意思。”
陈毅的知人善任让聂绀弩颇有感慨。他也意识到在前线自己难以发挥所长,加之频繁的战争环境不可能总是充满诗情画意,弄不好自己会成为部队的累赘。这样,聂绀弩告别了茅山,告别了陈毅,领到了20块大洋的路费,重返新四军军部。
与陈毅的再次见面是在春节期间,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所辖文工团在军部演出,陈毅等前线指挥官被请到军部会餐,观看演出。当时,聂绀弩也应邀到现场观看。但谁也没想到就是这场演出却引出了一段佳缘。
次日,陈毅看望聂绀弩,不免又谈起诗作。陈毅当即将一首昨晚的新作给聂绀弩看。新诗题为《赞春兰》,诗中写道:“小箭含胎初生岗,似是欲绽蕊吐黄。娇艳高雅世难受,万紫千红妒幽香。”显然这是一首爱情诗,聂绀弩看出了其中端倪。
原来昨天晚上演出中,台上一位女演员引起了陈毅注意并赢得了好感。她叫张春兰,相貌端庄,气质高雅,演技娴熟。陈毅可谓一见倾心。当晚即写下《赞春兰》诗。
聂绀弩觉得这是好事,表示愿意来当“红娘”,将陈毅的这份情感传递给她。正是聂绀弩的这份热情,专门将陈毅的《赞春兰》交到张春兰手中,才挑破两人心中那层薄纸,从而成就一段佳缘。张春兰以后改名张茜,成为陈毅妻子。他们忠贞不渝,风雨相伴,共同走过了30多年的人生历程。陈毅逝世后,聂绀弩专门写有《挽陈帅》诗三首,其一为:“浊浪淘沙百战鏖,进攻神速又迂包。江东子弟娴兵甲,天下英雄爱堑壕。谋画帐中虎皮椅,声威马上鬼头刀。东风暮雨周郎便,打打吹吹娶小乔。”这“打打吹吹娶小乔”之句,即是对当年作为陈毅与张茜间“红娘”历史的回忆与注释。

陈毅与张茜
聂绀弩刚参加新四军时还是有新鲜感的,部队的蓬勃朝气、战斗作风以及坚定的信念给他留下极深印象,他从中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但时间稍长,他的不适应即体现出来。毕竟他还是文人,率性而为、我行我素,部队的严谨生活和氛围仿佛与他有些格格不入。了解他的菡子说过聂绀弩的这种不适应:“在军营过组织生活时常常因为爱讲真话而与会议组织者的意图相冲突,严格的纪律他也不能适应。他骨子里其实是个自由随性的文化人,晨昏颠倒惯了,生活上不能适应部队生活。”这种反差决定了聂绀弩在短暂的兴奋过后,开始感到些许的惘然和落寞。
聂绀弩的情绪波动终于为周恩来所知。周恩来了解聂绀弩,也觉得在前线工作可能并不适合他,而在非军事机构从事文化工作或者创办报刊,将更能发挥他的特长。为此,周恩来专门致电叶挺、项英,提出将聂绀弩调出新四军的建议。电文大致内容为,如果聂绀弩在新四军不能有很大的用处,而他本人亦想离开部队的话,就让他到重庆来。叶挺、项英随即与聂绀弩谈话,征询意见。聂绀弩表示愿意前往重庆工作。叶挺、项英也很开明,在挽留未果的情况下表示尊重聂绀弩的选择。
聂绀弩就这样“转业”了。他与战友、文友依依惜别后离开了皖南,离开了新四军。聂绀弩后来辗转浙江金华、广西桂林最终抵达重庆,成为由周恩来、孙科等任名誉理事、老舍任总务主任的中国抗战文艺家协会的一名会员。聂绀弩依然用他的如椽之笔畅达胸臆,针砭时弊,呼唤抗战。
聂绀弩仍然是一名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