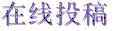又是一位献身者,又是一位殉道人。——陶行知去世了。
那天是1946年的7月25日,年仅55岁的他因为“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而永远地告别了人世。
上海、重庆、延安、香港、南京,乃至纽约、新加坡等诸多城市,纷纷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他的灵柩安葬在南京郊外的晓庄——当年他创办乡村师范学校的地方;他的遗墨“爱满天下”镌刻在墓前的牌坊上——当年他的奋斗目标与终生理想……

陶行知
无人不哭,无人不泣;无人不追思他所施予的爱,无人不感念他所付予的情。然而在他的四个儿子的心目中,则似乎存留着更多的遗憾和羡慕。长子陶宏说,他最终成为了“更大多数不幸人们的父亲”;幼子陶城说,他是真正做到了“损己舍家为人民”。——一个“爱满天下”的教育家,独独将他的爱遗漏于自己的家人。
“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
陶行知是1917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博士,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正式聘任的教务主任。《劳谦君子陶行知》一书的作者王一心这样写道:“考察中国20世纪一二十年代以降的与陶行知学历相仿的知识分子,他们所走的道路虽然因了国运的蹇剥、年代的动荡、外强的入侵而各有坎坷,但相较于陶行知所行之路,总还不失为常途。在抗战之前的二十年里,他们之中,除了学而优则仕的不算,单是安身于大学教席的,也多有物质生活优裕、社会地位甚高的黄金岁月。而陶行知,却出象牙塔而放弃了‘阳关道’,另选了一条崎岖的山路,披荆斩棘,踽踽独行。因此在这一群知识分子中,陶行知‘另类’的标记很明显。自然的,他的人生价值也恰恰在于此。”
这样的选择,对于当时尚在幼童时期的陶宏兄弟来说,却无论如何也搞不明白——父亲脱下西装革履换上布衣草鞋,他们是亲眼看见的;父亲离开大学校园奔赴穷乡僻壤,他们是亲耳听到的;最后全家因为父亲的关系而流离失所,而家破人亡,这更是他们所亲身经历与深刻感受到的。
长子陶宏写有一篇悼念文章《我和我的父亲》,但是他的笔常常会“跑题”,会不由自主地悼念起父亲之外的人来了——“在歌颂我父亲伟大的成就时,在哀悼他那种为大众谋幸福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时,千万可别忘了三个无名英雄:第一个就是我的姑母,第二个就是我的祖母,第三个就是我的母亲。在七年之内,她们为了父亲的事业而相继牺牲倒下。父亲是为事业拖死的,她们都是为父亲的事业拖死的。她们的精神同样是伟大的,不朽的。通过她们的牺牲,父亲才能放开手勇往直前地做去。”——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一丝淡淡的哀怨,隐藏着的是一丝抹不去的忧伤。她们毕竟是三个鲜活的生命,是三个同孩子们相依为命的亲人。
陶行知一生追求的是“博爱”,是“爱满天下”,对于自己最亲的三位亲人的离世,他岂能无动于衷?他曾万般痛苦地自责道:“母亲、文渼、纯宜,你们实在是三位最伟大的女性,实在是被我拖垮累垮的啊!”
陶文渼是陶行知唯一的妹妹,自幼进过学校,有理想,有抱负,更是坚定不移地支持哥哥的选择。1923年,陶行知给她写过这样一封信——“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然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
陶文渼为之而深受感动,并发誓全心全意支持哥哥的工作——1923年,陶行知推行平民教育,文渼则助其负责试验女子学校的工作;1927年,陶行知创办第一所乡村师范学校,文渼则助其开展晓庄周围妇女的工作。对于她的积劳成疾和英年早逝,陶行知痛不欲生,他说“我的心都要碎了”,“我的生命已经残废了一部分”。是啊,陶行知既然说过“晓庄是从爱里产生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那么他却偏偏没有将这个“爱”惠及到自己的妹妹。文渼倒下时,年仅35岁。
母亲曹翠仂,一位善良纯朴的劳动妇女,为了支持陶行知的事业,她同样是无怨无悔,不遗余力。1923年,陶行知于全国开展普及教育运动,年近六旬的她在小孙子的帮助下带头识字学文化;1926年,陶行知于乡村试办幼儿教育,她将自己六十寿诞时收到的贺金全部移赠给儿子作为创办学校的基金。然而,“爱满天下”的陶行知同样没能给母亲带来安慰和保护——1930年,晓庄师范被查封,陶行知被迫逃亡,此前他来得及为同事们做好各种安排,却来不及给自己的母亲和妻儿以任何的帮助。军警包围了学校,且四处扬言道,如果抓不到陶行知,便拿他的幼子当人质。年迈的母亲不顾自己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也不顾自己腿脚不便、行动不灵,借着黑夜的掩护,带领一家老小逃离虎口,于乡间的小路上仓皇奔命……
1933年,饱受颠沛之苦的母亲终于撒手人寰。陶宏不能原谅自己的父亲,他于文章中写道:“祖母中风的那天晚上,他一面守着祖母,一面还写一篇文章,写得很长,一直写到天亮。我起先还以为在给祖母写什么传记,后来才知道是在写长篇大论。”母亲病榻前的陶行知究竟写的是哪篇文章,今天已不可得知了。但是从时间上看,他为了普及教育而于江浙一带创办的工学团,此时正欣欣向荣、蓬勃发展——“乡村工学团是一个小工场,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在这里面包含着生产的意义,长进的意义,平等互助、自卫卫人的意义。它是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了一个改造乡村的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由此可见,此时的陶行知,心中只有工学团,只有工学团中那些穷苦的孩子们。母亲死后,他将为之购买的1000多元人寿保险全部提出,不是治丧事、办丧礼,而是购置了一架便携式电影放映机及一架与之配套的发电机,赠送给了山海工学团。陶宏写道:“这一部放映机和发电机不知道教育了几千万群众,不知道增加了多少抗战的力量。因为它们曾随着新安旅行团到达百灵庙、包头、陕西、山西、湖北、湖南、广西等等地方,留下几万里的足迹。”
汪纯宜是陶行知的妻子,陶行知曾有诗相赠:“久别重逢,思携手,离情共诉。羞涩涩,颊红心颤,默无一语。别日相思见时闷;闷来更比相思苦。问何时两个魂灵儿,如鱼水?义中情,何处去?敬离爱,便无据。试把二十四史从头数,哪个圣贤不多情?多情忍把今生负!看天边几个同心人,如我汝?”汪纯宜性格内向,寡言少语,多年来一直在家中默默地抚养四个孩子。然而,正是她的这一性格酿成了她最终的悲剧,也使她在为陶行知的牺牲上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痛苦。1930年,晓庄师范被查封,深深地刺激了她的神经,更何况谣言继之四起,或曰陶行知已被逮捕,或曰陶行知已被枪毙。汪纯宜的精神再也支撑不住了,她跑到夫子庙投河自尽,幸被发现,及时救起;她又大把大把地吞服安眠药,致使大脑慢性中毒,终于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姑姑去世了,祖母也去世了,神经失常的母亲不仅不能照顾别人反而还需要别人的照顾。无依无靠的孩子们仿佛一下子长大了,幼子陶城这样回忆那段悲苦凄凉的日子:“当时我年纪虽小,才八九岁,但我认为作为儿子应对慈母尽一片孝心与孝行。入睡前,我给慈母打来一盆热水让她洗脚,然后用手巾给她擦干,再给她盖上被子,叫她睡个好觉……”这时的陶行知在哪里呢?——他正在参与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正在酝酿与发动国难教育运动,并出任新成立的“国难教育社”社长。
1936年的年初,陶行知给不满18岁的次子陶晓光写信,建议他将汪纯宜送往上海“普慈疗养院”治疗。不曾想,现实的一切均非当初之预料,该院对于精神病患者没有任何的科学治疗方法,而是用天主教的教义及强迫患者向主祈祷来治病。4月23日的下午5点45分,汪纯宜痛苦地离开了人世,此时的陶行知又在哪里呢?——就在妻子咽气前的45分钟,他启程了。这次是应广西教育厅的邀请,前去进行普及教育的宣传,并作团结抗战的动员。就这样,孤苦伶仃的妻子没能最后见到丈夫一面,辞世前的悲凉可想而知……
其实,为了陶行知的事业而做出牺牲的又何止这三位女性?他的四个儿子同样享受不到本该属于他们的慈祥而温暖的父爱。在他们的记忆里,父亲只是那一封封的书信,还有那一行行写在信纸上的文字。
陶行知的朋友们对于他的这一做法多有指责——好听点的,说他是任其子女“自由生长”;刻薄点的,说他是任其后代“自生自灭”。就连好友翦伯赞也发出了这样的慨叹:“我从来没有看见他有过自己的家庭,我从来没有听见他谈到自己的儿女,更没有听到他谈到自己的生活。”其实,身为人父的陶行知又何尝不爱自己的孩子?他亲昵地依次称呼他们为“桃红”、“小桃”、“三桃”、“蜜桃”,他更将他们儿时的照片时刻珍藏在身边。但是陶行知毕竟是陶行知,他的爱绝对不会仅仅停留在自己孩子的身上。那天,他收到了一张母亲喂蜜桃吃饭的照片,立即便产生出了这样的联想:“我要把母亲爱蜜桃的心,本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推而远之,使凡如蜜桃的都能得蜜桃之爱护,享蜜桃之幸福。”——他的爱永远像雨露一般洒遍天下,洒遍每一个需要爱抚的孩子们的身上。
……就这样,为了一个“爱”字,陶行知年复一年地推行着他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国难教育;为了一个“爱”字,陶行知不知疲倦地奔波在众多的没有条件读书的孩子们中间。

陶母读书图
“我不是抱着石头游泳,而是抱着爱人游泳——越游越起劲!”
抗日战争爆发了!——中华民族在血与火中遭受着空前的凌辱与践踏,也在血与火中寻找着自己崛起与新生的机会。
更多的孩子成为了孤儿,更多的孤儿成为了文盲。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一向以关注和帮助不幸人群为己任的陶行知又有了他新的计划与行动。
陶行知是于1938年的8月31日回到国内的——此前他于英国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后因再次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不得不于海外滞留了26个月。就在他抵达香港的第二天,他当众宣布了回国后所要实现的一个重要“心愿”:创办难童学校,收容并培养具有特殊才华的幼苗。
如果说,此时陶行知决定创办难童学校的想法,仅仅是出于他在回国的轮船上看到了一位法国幼童具有超凡的音乐天才,能够随着不同的乐曲即兴表演不同的舞蹈的话,那么等他进入到内地,特别是于长沙、汉口、重庆等地的难童保育院中也发现了不少的中国儿童同样具有这方面天才的时候,他的心愿便更加坚定了。于是乎,设计规划、制定章程、核算经费、选择校址、延聘教师、招考新生……陶行知可谓是事必躬亲,宵衣旰食。
这是他亲自制定的《育才学校手册》——
宗旨 在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指导之下,教导学生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自觉觉人的小先生;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
方法 选拔有特殊才能之难童,在集体生活中,培养人才之幼苗,给以适当之阳光、空气、水分、养料,并除害虫,俾能发荣滋长。教育方法,注重教学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理论与实践并重。
……
1939年的7月,一所崭新的学堂——“重庆育才学校”终于在郊外凤凰山上的古圣寺中落成了。曾经在该校教过书的翦伯赞这样描述它:“寺院的规模很大,几乎占领了整个山头。坐北朝南,一连三重正殿。在正殿后面,还有一个藏经楼。四面绕以围墙,围墙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古之宫墙……当时育才学校的范围,不仅在古圣寺的围墙以内,在围墙以外,还有其他的机构。出山门往西的丛林中,有新置的石桌石凳,这是育才的好多座露天课堂。出山门往东,有一块大空坪,这是育才的运动场。在空坪的北端,有一个经过人工修整的天然土台,这是育才学生练习戏剧的舞台。此外,出山门往南,越过一个山坡,沿着一条小溪前行,有一座当地大地主的院落,这是育才绘画组学习的课室和宿舍。出山门往西的坑谷中,有几家农民的房子,这是育才音乐组学习的课室和宿舍。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寺南的三间草舍。这几间草舍,去寺约二百步左右,由寺院到草舍,有一条平坦的土路可通。这三间草舍,是陶先生新盖的图书室,里面藏有《图书集成》一部和其他的古书若干种。”
重庆育才学校,是陶行知于创办晓庄师范、自然学园以及工学团后的又一个重大的实践,是他于开展普及教育、乡村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后的又一个里程碑,也是他那“爱满天下”的胸襟与抱负的又一个飞跃与升华。
然而,这一次的办学却远远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它毕竟是在战争的年代,是在举步维艰的特殊时期。不说别的,光是轰炸——敌机对重庆的狂轰滥炸,就足以令人望而却步。为此多少人劝他冷静,劝他放弃,劝他明白这是“抱着石头游泳”。但是陶行知的回答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不是抱着石头游泳,而是抱着爱人游泳——越游越起劲!”
仍然是一个“爱”字!——育才学校成了他的“爱人”,成了他抱在手中死死不放的“爱人”。为了“她”,陶行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第一,千方百计战胜经济上的困难。
育才学校自开办之日起,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便是经济上的拮据。学校的经费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赈济委员会的定期拨款,二是保育院发给保育生的人头费,三是社会团体与知名人士的零星接济。然而物价的飞涨很快便严重地威胁到了它——仅以米价为例,两年中竟然涨了36倍之多。为此学校每月的亏空甚巨,伙房里几乎是无米下锅。但陶行知不会服输,经过全面的思考,他提出了三个解决困难的办法——
第一是“开源”。他说他就不信跑遍天下找不到一个愿为育才捐款的好心人。但这毕竟是“乞讨”,就连后来他也曾自嘲般地描述过这段尴尬的生活:“我成了一个体育家,每天练习百米赛跑。”碰壁,是家常便饭;但是一旦有了收获,他便会情不自禁地放声大笑:“又是一个胜仗!”“又是×万块钱!”
第二个办法是“节流”。面对着一贫如洗的学校,唯一可以“节”的就只剩下师生们的生活费了。于是他断然下令:三餐改为两餐,干饭改为稀饭,全校师生一视同仁。作为一校之长的他也毫不例外,乃至最后因营养不良而几乎晕倒时,也无任何特殊可言。
第三个办法是“生产自救”。学校于嘉陵江边租到一块生荒地,陶行知聘请当地的农民作指导,耪地、下种、除草、浇水……秋天到了,蔬菜和粮食大丰收,他下令:百分之七十交伙食团,百分之三十分给学生作为奖励,既改善了生活,又增强了学生们的劳动观念。
——陶行知终于胜利了!他战胜了经济上的困难,渡过了被他形容为“全身沉没得只剩下一个鼻孔在水面上呼吸”的艰难时期。育才学校不仅没有被溺死,而且还逐步建立起了小学部、初中部,甚至还有自己的游泳池和美术馆。
陶行知用他的爱挽救了育才,更用他的爱鼓舞着众人的意志——
我们有两位朋友:一是贫穷,二是患难。我们不但是在贫穷与患难中生活,而且整个教育理论都是它们扶养起来的。所以我有六个字供大家勉励:友穷,迎难,创造。
第二,坚定不移排除政治上的干扰。
作为两次被国民党政府通缉的人物,陶行知的一言一行始终受到监视,哪怕是已经进入国共合作的新时期。果然,没过多久政治上的压迫便接踵而来了——先是成立于1933年的新安旅行团被强令解散;继之是成立于1938年的生活教育社被强行摘下牌子;等到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的教育部则直接挥舞着斧头向育才学校砍杀过来。
第一步,他们先来软的——以“利”相诱。教育部长陈立夫满脸堆笑地对陶行知说:“只要你同意将育才改为公立学校,经费可由教育部直接拨给,再也用不着你去四处奔波八方筹募了!”但他的附加条件是:必须按国民党规定的训育制度办学,并由教育部直接派遣训育主任。陶行知当场拒绝了他。他向师生们这样解释道:“我只要向国民党政府稍微低一下头,不要说办一所育才,就是十所也办得起来。但是我们要的是自己办学校,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办学校。所以一定要做到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这样,育才学校的那份立案申请,足足被北碚区署拖延了一年、被四川省政府拖延了两年半之后,才获得了批准。
第二步,他们再来硬的——以“势”相逼。教育部强行下达了命令:凡国统区内的学校必须建立国民党的区党部。陶行知明白硬顶是没有用的,于是他请来冯玉祥帮忙。这位当年曾积极支持他创办晓庄师范的老朋友,果然有办法:他弄来了五张空白的国民党党证,于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影子党部”便在校园内成立起来了。教育部并未甘心,后来又多次派人伪装进步,企图打入育才的内部,结果都被陶行知以“考核成绩不佳”、“不适宜作教师工作”为由而拒之门外。
第三步,他们请出当地的县政府——以“阴谋”相破坏。凤凰山属于合川县,育才在开办之前即与古圣寺签订了25年期限的租用合同,不曾想县政府竟于半路跳将出来,强令古圣寺收回房产,另作他用。这一手段足足困扰了陶行知将近两年,他一方面延请律师,准备诉诸法律;另一方面则发动冯玉祥、司徒美堂等知名人士进行呼吁,以期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
——陶行知终于胜利了!他战胜了政治上的压迫,排除了政治上的干扰。他用他的爱保护着育才,更用他的爱激励着众人的斗志——
晓庄是从四个帐篷办起,到三十个茅棚,那才是创造。山海工学团却连一个茅棚也没有造,也没有堂皇的古庙给我们享受,那也是真正的创造。老实说,如果地方的朋友要整个的古圣寺,我们也丝毫不留恋地让给他们。这样我们再来住住帐篷,过过野人生活,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第三,孜孜不倦摸索育才的经验。
经济上摆脱了困境,政治上摆脱了干扰,这固然是育才学校值得骄傲的地方;但是作为一所以培养特殊人才为目标的学校,它的成功与否更在其“产品”的质量与数量上。曾经两次应聘于育才的史学大家翦伯赞,这样评价与赞赏它的“奇迹”:“十几岁的孩子,能够在座谈会上面谈局势,从国内到国际,从政治到军事,明如指掌;能够写出文学作品;能够自编剧本,自己导演;能够自己作曲,作歌;能够写生,速写;能够画出星宿的图谱……假如有一天,我能三访古圣寺,而我又有权更改这座寺的名字,我一定把它改名‘陶圣寺’。”
翦伯赞的的赞扬并非空言,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来看,育才学校的创办确实令他达到了又一个高峰。他以他的爱先后招收与培养了数百名的难童,更以他的爱创出了一套崭新的“人才教育”与“创造教育”的思路和方法。
什么是“人才教育”?陶行知在《教育纲要草案》中详细地制定了它的内容:“育才学校办的是人才教育,分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自然等组。我们选拔具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在开始时便同时注意一般基础教育与特殊基础教育。前者使儿童获得一般知能及优良的生活习惯与态度;后者给予具特殊才能之儿童以特殊营养,使其得以发展而不致枯萎。”
这一做法确实是大胆的;而这一大胆又确实缘于战争的特殊环境。以其课程的安排来看,它一共分为两类:一类是与一般学校相同的“普修课程”,如语文、数学、外语等等;另一类是“特修课程”,即专业教师为学员们特别讲授的内容,比如文学组有名著选读、作家研究,音乐组有钢琴、乐理,绘画组有素描、写生,戏剧组有表演、化装,社会组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等。为了保证教学的质量,陶行知亲自出马,广泛聘请著名的专家学者前来任教,这里有音乐家贺绿汀、任光,戏剧家章泯、舒强,美术家陈烟桥、华君武,舞蹈家戴爱莲、吴晓邦,文学家艾青、力扬等等;至于应邀前来作学术报告或开专题讲座的更是数不胜数:郭沫若、邓初民、茅盾、田汉、翦伯赞、周谷城、光未然、何其芳、许涤新、马思聪、丰子恺……这样的名单就连一般的大学也是望尘莫及。
为了防止偏颇,陶行知更是时时不忘提醒大家:人才教育的目的绝不是培养“人上人”——“我们的孩子们都是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得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为老百姓造福利;他们都是受着国家民族的教养,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贡献给整个国家民族,为整个国家民族谋幸福;他们是在世界中呼吸,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帮助改造世界,为整个人类谋利益。”为了实现这样的培养目标,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学生们走出教室,走出校园,为广大的工农群众服务。据当年的学员回忆:“在学校附近的农村、矿山,我们陆续建立了几十个农民识字班,参加识字班学习的有孩子,但大多数是青年农民,还有一些矿工。我们不仅教认字,还讲革命道理,教革命歌曲。我们还访贫问苦,给农民送药治病,发放寒衣,和农民建立了血肉般的感情。”……由此可见,陶行知开展的“人才教育”是成功的,在最为困难的战争年代里,他不仅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特殊人才,而且为民族培养了大批合格的普通劳动者。

重庆育才学校校门
什么是“创造教育”?陶行知这样解释道:“创造教育是在儿童自身的基础上,过滤并运用环境的影响,以培养加强发挥其创造力,使他长得更有力量,以贡献于民族与人类。教育不能创造什么,但它能启发解放儿童创造力以从事于创造之工作。”为此,他提出了解放儿童创造力的五个方面——即他们的头脑、双手、嘴巴,以及空间和时间;也详细地制定出孩子们应该达到的二十三项“常能”——会领导工作、会发表演讲、会清理账目、会管理图书……
1941年的8月1日,陶行知在育才学校正式宣布“创造年”开始;同年9月,他又推行了“少年研究生制”,并将其作为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与“人才教育”相比,这一步迈得更大也更勇敢了——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何曾有过于中学阶段即培养研究生的先例?但是陶行知就在敌人飞机的狂轰滥炸之下,就在经济与政治的巨大压迫之中,开始了这项令人瞩目的实验。
首批少年研究生共有27名,这是经过个人自愿报名、教师综合测试、学校全面审核之后而确定的。他们可以提前修完各自的课程,以专心从事学术研究;他们可以自由借阅学校的各种藏书,不受时间与数量的限制。陶行知自己则亲自指导他们如何做卡片,如何查资料;更亲自为他们联系导师,安排实习。15岁的朱振华在翦伯赞的指导下完成了考古研究《古圣寺有多少岁》,后来又将研究方向转向苏德战争,撰写出了20万字的论文《苏联必胜》,颇令刚刚卸任回国的驻苏大使杨杰将军惊叹不已。社会组的张旭东研究的是《英美苏三国外长会议》,他不仅在“苏德战争谁胜谁败”的辩论会上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随时将研究的心得张贴在壁报上,以征求同学们的意见;后来陶行知将他推荐到《新华日报》当记者,再后来他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名副军级的政治干部……少年研究生制的初步探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他们中间除了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性的人才外,还培养出了不少创作人才,例如后来成为作曲家的杜鸣心、成为剧作家的张玮等等。小小年纪的他们,先后创作出了4个剧本、27首歌曲;其中的方言话剧《啷格办》,更是于社会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陶行知胜利了!他用他的爱赢得了育才学校的成功,赢得了“人才教育”与“创造教育”的成功,也赢得了对于未来的坚定信心——
我现在觉得我是一只狮子,在人们都睡着的时候,巍然雄视一切,为夜之主,有整个的宇宙待我整顿,我是何等的高兴啊!……我有力量追求一切真善美和真善美的一切!

1946年6月,陶行知于上海发表反内战演说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育才学校的孩子们徜徉在爱的河流之中,翱翔在爱的天空之下。他们一个个长大了,一个个成才了。
但是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是这样的一幕——“我悄悄走到池塘边,来到陶先生所住的一栋草房的窗前。我看见他正伏案写着什么,却打着赤膊。我暗自纳闷,天气并不太热,为什么要光着脊背写作呢?我去问一位老师,他告诉我,陶先生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办教育事业上了,自己只有一件像样的白布衬衫,到了夏天就换洗不过来,往往一面办公,一面把衬衣洗了,晾在一边,有事时才穿上衬衫出去。”这是学生高缨的回忆。
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年冬天,陶先生唯一的一件大衣被小偷偷走了,“晚上回来,他和我们围坐在一起闲话,很诙谐地跟我们说,以前他乘坐公共汽车最怕人多拥挤,现在如有两辆汽车同时到达,他便向人多的车上去挤:人多热气大嘛!等我们回味过来陶先生这句话的意思时,都沉默不语了。”这是教师丁右涵的回忆。
——这,就是陶行知自己的生活!一个完全有条件过上富裕日子的留美博士的生活!陶行知无怨无悔,他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1981年,在纪念陶行知九十诞辰的大会上,他当年的学生、后来的国务委员张劲夫于发言中称赞他的精神为“损己利人”。——一个“损”字,包含了多少的内容啊!他“损”掉的不仅是母亲、妹妹、妻子的生命,不仅是儿子们所渴望的父爱,更有他自己的一切,甚至包括健康。
……他终于倒下了,他终于将自己也彻底地“损”掉了!那天是1946年的7月25日,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立即奔来,他在详细地询问了医生之后,得出的是这样的结论:他是因“劳累过度”而死的,是因“健康过亏”而死的,是因“刺激过深”而死的。
他是完全可以不死的——他死时还不满55岁!但是他却把爱给了抗战的事业,给了更多的人们,唯独没有留给他自己……
毛泽东称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宋庆龄称他是“万世师表”;
董必武称他是“当今一圣人”;
郭沫若称他是“孔子之后的孔子”……
但他还是他——一个心甘情愿将爱洒满天下的教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