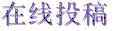梁漱溟,1893年出生,1988年去世,享年95岁。
当今的人们对于梁漱溟的了解,更多的是他的性格——宁折不弯,敢于仗义执言;刚正不阿,无惧廷争面折。然而,梁漱溟自己却这样解释:我的祖上是蒙古人——“从种族血统上说,我们本是元朝宗室。”原来,在他的血管里流淌着桀骜不驯的蒙古民族的血,在他的身体里蕴含着耿介执拗的草原骁骑的基因。
当今的学者对于梁漱溟的评价,更多的是他的学问——国学家、哲学家、思想家……然而,梁漱溟自己却反复说道:“我无意乎学问。”“我不是学问家。”原来,他所希望于自己的竟是这样一个论定——“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他说了:“我自14岁进入中学以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于是乎,性格中的倔强与刚毅支撑着他不断地去探寻心中的那两个追求,心中的那两个追求又反过来不断地增强着他性格中的自信与自负。
于是乎,他的一生便这样走了过来;又于是乎,他对世人发出了这样的“狂言”——
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我们自有立国之道”
梁漱溟所诞生的年代为清末光绪年间,为此有学者称他是“具有古代‘士’的理想风范的新型知识分子”,抑或说,就是“新时代的‘士’”。
然而,最初之时梁漱溟却一心皈依于佛教,想从“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中探寻“人生问题”。不料,1917年的春夏之交,梁漱溟南游时遭遇一场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现实强烈地震撼了他;回到北京之后,他奋笔写下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不仅表示出坚决与过去的出世思想告别,而且表示出希望天下的士人都能挺身而出,以“济苍生”为己任——
吾曹不出,悉就死关;吾曹若出,都是活路。而吾曹果出,大局立转,乃至易解决之事,乃必成功之事。今日之宇内更无有巨大力量如吾曹者,握全国之枢机者不在秉钧之当局,而在吾曹。嗟呼!吾曹其兴起!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好大的口气啊!——胡适读后慨然曰:“梁先生这个人将来是会革命的!”拖着条小辫子的辜鸿铭也情不自禁地称赞道:“有心人哉!”
梁漱溟前去山东省第六中学讲课,当年的学生清楚地记得该时的情景:“在六中大礼堂北面有一棵老槐树。老槐树生在一个土坛上。老槐树前边放一张教桌,树上钉一块黑板,供梁先生写字之用……梁先生讲到军阀混战,人民生活痛苦时,怒气冲天,手拿小草鞯拍打着桌子,泪水从眼镜后面像雨点似地流下。这时全场寂穆,听不见一点声音……”——应该说,就从这时起,梁漱溟开始由“人生问题”转入到“社会问题”的思考了,他要以“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气魄,为中国寻找一条改革的途径。
……这是一个“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阶段——“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皆在静默,唯间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地感觉心地清明、兴奋、静寂,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自己,只要能兴奋反省,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一刹那。”这是后来梁漱溟对于这段生活的回忆,但是他的这一“反省”,却是极其漫长的——前后花去了整整10年的时间;他的这一“刹那”,也是极其艰难的——每每都是茫无崖岸的失望。但是,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它令梁漱溟顿感彻悟,顿感觉醒,也顿感自己找到了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途径——
于一向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者,现在断然地否认他了;于一向之所有见而未敢遽然自信者,现在断然地相信他了!否认了什么?否认了一切西洋的把戏,更不沾恋!相信了什么?相信了我们自有立国之道,更不虚怯!
详言之,便是西方的政治制度、教育方式以及所走的都市化道路,都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要想摆脱目前的困境,解决现实的问题,只有依靠中国人自己,依靠中国文化中所固有的东西。——梁漱溟所认定的道路,不是别的,就是“乡村自治”(后来又称为“乡村建设”),他坚定不移地相信:这,才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梁漱溟的这番思索,来自于这样的一个认识:几千年来,中国的社会只能算是一个“村落社会”,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散漫无组织。因此要想改革,必须从农村开始,这样才能一步步地走向有组织的社会。具体来说,就是在经济方面实行社会化,在政治方面实行民治化。数十年之后,梁漱溟在回顾自己的这一改革时,再次将他的蓝图进行了归纳:“中国政治问题须要分两步解决。树立统一稳定的国权是为头一步。有此统一稳定的国权即可进行有方针有计划的建国——建设一个政治上达成民主主义,经济上达成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必须到建国完成,方为政治问题的完全解决,是为第二步。从开头到末尾说作两步,却全靠一个乡村建设运动贯彻于其间。乡建运动实是建国运动;它为自己创造出它在政治上所需的前提条件——统一稳定的国权。于先,又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建设而推进政治的民主化,以至奠立完美的民主政治制度于后。”再具体一点便是:“我所想的宪政的新中国,必须从地方自治入手,而地方自治又必须从团体自治入手,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实现。我梦想的团体自治是合作社;这种合作社主要是生产合作,也包括消费合作、信用合作。”
梁漱溟既然将自己定位于“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那么他很快便亲自动手,脚踏实地地干起来了。——最初,他选择在广东进行他的“乡治”实验,但《建议书》却迟迟批复不下来;继而,他又选择在河南创办“村治学院”,但因“中原大战”的爆发而被迫关闭;最后,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出面,给予了一定的支持,他那盼望已久的“乡村建设研究院”才终于建立起来。
梁漱溟所绘制的这张蓝图,真可谓既宏伟又详尽——第一,“乡村建设研究部”的任务是:负责理论上的研究与探讨,并制定出相关的方案和政策;它面向全社会招生,对象为大专院校的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者。第二,建立“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具体的任务为:负责培训参加“乡建”的干部人选,其招考的对象为乡村中的中学毕业生;据统计,“训练部”一共培训了1040人,另有短训班学员1300人。第三,在下属的实验区里,即邹平、菏泽、济宁三县,全面推行其具体的乡建计划,主要有:地方行政改革实验、地方自治推行实验,以及包括振兴产业、发展经济、开发民智、改善风俗等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改进实验……
由梁漱溟亲自指导和挂帅的这一乡村建设运动,正式开始于1931年的6月,结束于1937年的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尽管它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带有改良主义的味道,但是作为一种尝试,曾于国内掀起了一股热潮。——据统计,该时从事农村工作的团体达到600多个,各种试验区多至1000余处。至于梁漱溟自己,更是以“出家的精神”投入到这一工作当中——“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动他的心肝,牵动他的生命……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朋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般的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的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
的确,为了实现这一改革中国社会的计划,梁漱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1935年,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客死于邹平,虽说是因为难产,但如果不是在这僻远的实验区,而是在北平,在有着先进设备和著名医生的医院里,总不至于无力回天!
于长茂曾经是训练部的学员,他回忆道:“在两年学习中,每日亲听先生讲授《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等课。在讲授时梁先生忧国忧民的心情每每流露于言表。每日授课三四个小时,其苦口婆心谆谆诲人的精神,以及那精湛的论述和铿锵有力的语言,深深打动着每一个受教育者的心。由于先生耳提面命,言传身教,我和同学深受感化,过去热心向往城市生活的同学,经过一二年的教育,结业后都愉快地到贫穷落后的农村去工作。”——有了这样的收获,无疑是梁漱溟最大的欣慰。

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手稿
“应当在如何让敌人不容易毁灭我们处着想”
战争爆发了!战争迅速地摧毁了原有的一切!
梁漱溟苦心经营了六年的乡村建设事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不得不被迫宣告结束。然而,此时的梁漱溟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沮丧:一则,眼前毕竟是一场关系到全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它远比乡建运动要重要得多;二则,这也是一个考验国人立场的关键时刻,它更需要“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气概与抱负。更何况对于梁漱溟来说,乡建也好,抗战也好,其努力的方向和工作的重点都是一致的,即他所说,是“一贯下来的”——
我认为中国不应当在如何摧敌处着想,而应当在如何让敌人不容易毁灭我们处着想,乃至在我们被毁后如何容易恢复上着想。尤其要紧的是在调整内部关系,以树立应付(国际)环境的根本。
那是1937年七七事变前的6月13日,梁漱溟应邀在成都作了一次《我们如何抗敌》的演讲。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有些朋友不明白我们乡村工作和应付当前国际问题的关系,嫌我们缓不济急,所以要特地指明我们正是准备抗敌,才从事乡村工作之理。”——这个“理”不是别的,它就在于:抗战需要兵力,需要持久的军备,而这些只有通过乡建运动才能完成——“我们的乡村建设工作,正是切近农民日常生活加以教育及组织,健全地方下层机构,为政府统治运用之准备;正是解除一点农业上的痛苦,培养农民爱国情绪,并增强其抗敌能力的。”由此可见,在梁漱溟的心目中,“乡建”与“抗战”之间具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就是他所强调的:“在如何让敌人不容易毁灭我们处着想。”
应该承认,梁漱溟的这一思考确实具有深远的意义——他的着眼点,是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如何将他们迅速地发动起来,成为抗敌的中坚力量。
于是乎,梁漱溟变了——这个一向远离政治的书生,开始投身于政治活动;这个一向远离官场的文人,开始步入参政机构。不为别的,只为能够借助政府的力量,更快地实现这一目标和理想——
第一,梁漱溟出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认真拟定出“非常时期乡村工作计划大纲”。
出于抗战形势的迫切需要,以及爱国民主人士的一致要求,1937年的8月1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做出决定: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全国国防的最高决策机关,并于其下设立“国防参议会”,作为它的咨询机构。梁漱溟与张君劢、胡适、沈钧儒、黄炎培、毛泽东等25人被聘为首批参议员,8月17日第一次会议于南京召开。
能够步入如此高层的政治机构,梁漱溟非常积极,也非常认真。他迫不及待地拿出了自己的提案——立即成立一个负责动员工作的机构,以将发动民众与组织民众的大业纳入正常的轨道。为了能够更加清楚地阐明自己的意见,他又提出了八点建议,以期将这一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下去。不承想,他的发言几乎无人理会——“有一位性急的朋友,起来阻止我,不要说下去。他认为那时上海的炮火正紧,应当商量军事,商量外交,你怎么说这个呢?当时会议席上除参议诸公而外,政府各部长均在座,看神气能理会我意见的人很少。大约他们都觉得我‘文不对题’吧!”
梁漱溟并没有感到失望,他似乎也认为自己的建议“说早了些”。不久,他与黄炎培、江问渔、晏阳初等人获得了一次面见蒋介石的机会,作为曾经共同从事乡建工作的同仁,他们便一致进言,希望政府能够更多地关心农村,并以知识分子为基干组成乡村工作团,进行宣传与发动。这一次大大出乎梁漱溟的意料,蒋介石不仅同意了他们的意见,而且还令其尽快拟定出详细的计划。——“我们四人奉命之后,曾数度集议,一度访陈立夫部长。又承政府将关于动员的一切计划草案法令送来参考。乃一面就动员说话,对于那些法令章则,条陈了十几条的意见;一面就乡村说话,提出一个非常时期乡村工作计划大纲,请政府择行其一。”……然而等到梁漱溟将大纲起草完毕,战局却又急速地发生了逆转——国军已退出上海,政府正忙于西迁,梁漱溟还能说什么呢?他除了叹气还是叹气。
第二,梁漱溟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认真提交了有关战时农村问题的建议案。
由于国防参议会的人数和职权都十分有限,不具备真正的民意机关的性质,在各党派、各团体及众多社会名流的强烈要求下,1938年的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立即成立国民参政机关的决议,以集思广益,团结更多的抗日力量。7月6日,梁漱溟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并与张君劢、沈钧儒、董必武等24人当选为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乃至于后来的第二次至第五次会议上,梁漱溟亦连连当选。
身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梁漱溟颇感责任重大,他迫不及待地围绕着战时农村问题又拿出了一个建议案和三个询问案。在建议案中,他指出:如今抗战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无不依赖于农村,但是农村中所存在的问题相当严重——交通运输不通畅,行政机构不健全,农村负担过重,农民生活贫困……为此,他“拟请行政院召开战时农村问题会议”,以“亟筹整理补救之方”;他还要求会议结束后设立一个常设机关,以负责落实这一问题的解决。在三个询问案中,他分别询问了这样几个问题——政府在全力发展农村经济方面有哪些统筹规划?在改善和充实农会组织方面有哪些“至计”?在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以适应战时需要方面有哪些举措?……然而,最终的结果却使梁漱溟大失所望——“原案经审查会修正(增加与会人员)通过,送经大会照案通过。秘书处咨送政府,经国防最高会议发交行政院核议。行政院又交经济部核复。经济部翁部长文灏、何次长廉,私人请我商谈一度后,具复行政院认为事实可行。行政院又照样具复于国防最高会议。国防最高会议亦曾将经济部行政院的核议可行通知国民参政会秘书处。但除公文往来复去而外,事实上并无下文。”
梁漱溟没有死心,等到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召开时,他继续为农民说话,又提交了一份《改善兵役实施办法建议案》——“对西南大后方来说,当然以补充兵员、多多征集、好好训练为第一事。但兵役问题,恰办得不好,谈者莫不疾首蹙额。我们做乡村工作的人,对此不能坐视,不能躲闪,而为了抗战亦非给国家求得好兵员不可。于是我就留心兵役改善的研究,思所以尽力之道。”梁漱溟所说的“留心”,便是他亲自于四川乡间进行调查,并且召开了各种人员的座谈会,以求寻找出一个既能为国家征募到好的兵员,又能为农民减轻一定负担的办法。然而,它却再一次地令梁漱溟大失所望了:提案送出之后,如同石沉大海,久久没有下文……
第三,梁漱溟利用自己所具有的特殊身份,进行广泛的考察,以了解各地农村与农民的现状。
这样的考察先后有两次——
第一次是在1938年的1月——即由国防参议会下达给各参议员的任务。梁漱溟自请视察陕西和河南,但他真正的目的却是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一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二是对于中共负责人有意见要交换。”但是,当他踏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之后,却又“本性难移”了,他仍然将注意力放在了考察农村与农民的现状上。他发现那里的物质环境“极苦”——“举目所见,荒凉凄惨”;但那里的精神气象“确是活跃”——“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爱唱歌,爱开会”,“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他更发现那里的政制非常“民主”——“上自政府主席,下至村乡长,都是选举出来的,并且各级都有议会”。这一发现对长期从事农村研究的梁漱溟来说,既新鲜又好奇,可惜的是他没有时间去作进一步的调查,但是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还是插入了不少有关乡村建设的讨论,而且“彼此都很有兴趣”。
第二次是在1939年的2月,这一次完全是出于他本人的申请——由于屡次的提案都没有下文,梁漱溟深感“纸上谈兵”的无用,他请求前往华北与华东各战区视察,目的之一便是“研究乡村在敌后起的变化”,及其“对于未来大局政治的影响”。这一次的巡视长达八个月之久,梁漱溟的足迹踏遍了皖、苏、鲁、冀、豫、晋6省,共50多个市县。谈到体会,他说,第一点就是“老百姓真苦”——“怕是倾若干泪和血亦诉不尽,任何一支笔,任何一张口亦形容不尽。”谈到感想,他还是说,第一点就是“中国老百姓太好”了——“为了抗战,他们受尽苦难,却没有怨恨国家、怨恨中央之意。对于游击队(所谓省保安队等亦在内)的随时筹措给养、对于我们这样的过路军政人员的沿途提供招待,他们均主动负担,且承认是完全应该的。”也正是因为受到了这样的感动,他说,他的第二个感想,便是今后的工作“非普遍从乡村求进步不可”。——他为他所看到的“民生之穷苦,风俗之固陋”而痛心,更为“民国三十年来正经事一件没有做”而扼腕;他希望能够继续开展乡村建设,“有计划地用社会教育普遍推进建设工作”,以求得“社会进步”。遗憾的是,梁漱溟本来还准备继续进行一番更加深入的调查与研究,但由于环境的日益险恶,以及敌人的频频扫荡,不得不忍痛放弃了。
针对梁漱溟的不懈努力,冯友兰曾概括出这样两句话:“以发扬儒学为己任,为同情农夫而执言。”的确,这正是梁漱溟的可贵之处——自打1927年他“悟”出了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的方法之后,便时时刻刻将农民大众的问题放在首位:战争爆发之前,他考虑如何开展乡村建设,以提高农民的觉悟,改善农民的生活;战争爆发之后,他考虑如何体恤农民,如何发动农民,使之成为“敌人不容易毁灭我们处”。
然而,梁漱溟很快便“退隐”了。他的这段短暂的“参政史”,与其漫长的人生旅途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以其收获而言,他是“空空如也”;以其教训而言,他却是“满载而归”。他并不后悔,他终于明白了“政府”是怎么回事,“提案”又是怎么回事;他也并不遗憾,作为一名参政人员,他尽责尽职了,也全力以赴了。

梁漱溟先生家庭照(第二排左二为梁漱溟)
“推动两大党团结抗敌合作建国”
1941年,梁漱溟写下一篇名为《我努力的是什么》的文章,对自己四年来所付出的“努力”做了一个总结:“一是国内的团结;二是民众的发动。”至于二者的排序,他又作了一番“说明”——“我第一个念头原在发动民众,因为意想中全国一致对外不成问题。后来晓得事情不这样简单,还必须先求团结才行。否则彼此猜防之心未泯遽动手发动民众,愈发动即愈冲突,冲突大了,国事便不可为。”——这是实话,也是令梁漱溟最感焦虑的事情:在后方参政时,他的提案屡屡得不到落实,这颇令他认识到“党派问题是一切事情的总障碍”;在前线视察时,战场上屡屡发生磨擦,这更让他感觉到“党派问题尖锐严重”。
其实早在1938年的1月,梁漱溟前往延安考察时,不便公开的目的亦即在此了——“所谓考察者,不是考察别的,是专为考察共产党的转变如何”;“所谓交换意见者,不是交换旁的意见,是专为求得国家进一步的统一,而向中共负责人交换意见”。前后20天的时间,梁漱溟以亲身的感受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第一,“他们的转变不是假的,不是一时策略手段如此,他们不愿再事内战的情绪很真切”;第二,他们的转变却又不深,“他们仍以阶级眼光来看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问题”。为此,梁漱溟当时即向中共领导人提出了应该确定国是国策的主张——“假如国是国策定下来,则党派问题即将得一根本转变。”毛泽东等人均表示了同意。
然而,到了1939年的秋天——亦即梁漱溟从华北与华东战场视察回来之后,他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两党军队频繁磨擦的切肤之痛,也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艰巨责任。于是,他一方面去拜见蒋介石,汇报自己的想法;另一方面去会见中共代表,交换彼此的意见;再一方面则约见国共之外的“第三者”人士——“第三者于此,无所逃责,而零零散散,谁亦尽不上力量。故第三者联合起来,共同努力,为当前第一事。”
借助“第三者”的力量进行调解,这是梁漱溟最初想到的办法;将“第三者”的力量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坚固的阵营,这是梁漱溟后来形成的认识。数十年之后——亦即1980年,已是87岁高龄的梁漱溟在向美国学者艾恺回忆起这段历史时,再次坦言道:“我很怕引起内战,引起内战就妨碍了抗日。抗日期间不可以有内战啊,所以我就先搞‘统一建国同志会’,后来搞‘民主同盟’。旁人误以为我是想搞一个自己的党派,其实不对。我不认为中国在两大党之外,还要一个第三党派,我没有这个意思。民主同盟不是第三个党派,是什么呢?是想推动两大党团结抗敌,合作建国。”
于是乎,当农村问题的提案搁浅之后,梁漱溟便矻矻以求地为这件事情奔走——
1939年的11月下旬,梁漱溟联合中国青年党的左舜生、李璜、曾琦,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胡石青、罗文干,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中华职教社的黄炎培、江恒源、冷遹,以及无党派民主爱国人士张澜、光升等人,在重庆正式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并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与《统一建国同志会章程》。
1940年的4月,梁漱溟于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上提交了《请厘定党派关系,求得进一步团结,绝对避免内战,以维国本案》。他在自述中说:“其实在我早知问题解决非易,并不存何等奢望。我只望在会内会外造成强烈不许内战的舆论空气,俾军事行动收敛一下,而寻求合理解决途径。”
1941年的3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召开。由于年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共两党的冲突达到顶峰。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等人向秘书处提交了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意见,国民党方面则拒绝接受。为此,梁漱溟积极地奔走于两党之间,并代表“第三者”方面起草了4条意见;其核心主张是,立即成立一个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特种委员会,检查并监督对抗战建国纲领的执行情况,但最终却未能实现。
1941年的3月19日,经过数月的酝酿与准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重庆秘密成立。会议讨论通过了它的《政纲》和《章程》,成立了领导机构。梁漱溟当选为中央常委,黄炎培为常委会主席。——谈到它的“发起”,梁漱溟是这样讲述的:“同盟之发起,在民国29年12月24日。是晨重庆报纸揭出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人选名单,既于名额一再扩充,而上届在选之党外人士或敢言人士则屏除不少,殊失人望。余与黄炎培、左舜生两公不期而相会于重庆新村4号张君劢家。彼此感慨同深,遂发同盟之议。”后来,梁漱溟又撰文详细地叙述了那天早晨他于读报时的复杂心情:“……这样引起我对国民党一种非常大的悲观。因参政会本来形同虚设,若多罗致几个党外人物,在国民政府至少亦可装点门面。偏偏连这一点作用都不留,而给大量党内闲人挤进来吃闲饭,国民党的没出息可算到家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最初,它包括了“三党三派”: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派、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人士;1942年,救国会正式加入。
1941年的5月20日,梁漱溟只身前往香港,奉命创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9月18日,《光明报》正式出版;10月10日,《光明报》公开发布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消息。为了预防新闻检查机关的扣检,其成立的“启事”以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均刊登在了广告栏内。与此同时,这些文件亦被翻译成英文,通过各国的驻港记者迅速传至海外。
1942年初,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光明报》被迫停刊,梁漱溟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之下,经澳门、台山、肇庆、梧州等地返回桂林。周恩来托人带信,邀请梁漱溟前往苏北或其他的中共根据地,并表示愿助一臂之力,帮助他建立起乡村建设的据点或民主同盟的据点。梁漱溟拒绝了——“我内心上觉得我不能靠近那一边。靠近那一边,就要失去或削弱我对广大中国社会说话的力量,对于我要广泛团结全国各方面来说,是不合适的。”
与此同时,国民党也前来邀请梁漱溟,参加筹办宪政实施协进会,他同样拒绝了——在《答政府见召书》上,他公开表示:“执政党对于党外之压制,转迫转紧,浸至无所不用其极。人不入党,几不得以自存;言不希旨,绝难宣之于笔口……政府诚有取于民主精神,政府自实践之,何用许多人来筹备!”
1944年的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梁漱溟当选为中央常委、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千家驹回忆道:“我是在1944年冬参加民盟的,介绍人即为梁先生。与我同时参加民盟的还有欧阳予倩、莫迺群、陈此生、张锡昌、周匡人、徐寅初诸同志。我们都填写了入盟志愿书,并签名盖章。志愿书写好后,当场焚毁,因为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民盟还是地下组织,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好,既履行了正式入盟手续,又不露痕迹。我不知道这一办法是不是梁先生想出来的。”
1946年的1月,梁漱溟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起草《中国民主同盟关于军事问题的提案》;3月,再访延安,与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会谈;5月,接任民盟中央秘书长,参与国共和谈;7月,赴昆明调查李公朴、闻一多被杀案,公开要求取缔特务机关——“这种机关不取消,民主同盟不参加政府……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我在这里等待着他!” 11月,梁漱溟辞去民盟秘书长的职务。
……

晚年的梁漱溟
那是1980年盛夏的一天,87岁的梁漱溟在回顾自己的一生后慨然说道,他没有遗憾了,因为“想做的事情都做了”,“也还都算是顺利”;这其中便包括“奔走于两大党之间”,“发起民主同盟”。——的确,这正是梁漱溟的欣慰之处、自豪之处。为了争取团结抗日,为了反对独裁统治,他挺身而出,担负起这一艰巨的使命;他殚精竭虑,哪怕是举鼎绝膑也在所不惜。
我的生命就寄于责任一念。处处皆有责任,而我总是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久而久之,我所关心的,旁人往往不如我关心;我所能做的,旁人往往不如我能做;好像责任集中于我一身。既有“四顾无人”之慨,不免有“舍我其谁”之感。
还是如此的自信与自负——这就是梁漱溟!“本性难移”的梁漱溟!狷介傲岸的梁漱溟!
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后的一位大儒”;有人说,他是“新时代的士”。梁漱溟则说:“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他更说:“区区日寇,不足以扰我也!”
是的,面对着惨烈而残暴的侵略战争,面对着“舍我其谁”的历史重任,又有谁能够“扰”他呢?又有谁能够“扰”得了他呢?——在华北考察时,他经历了敌人的多次扫荡,却神色自若,从容不迫;在香港办报时,他经历了生死的凶险逃亡,却履险如夷,若无其事;在桂林讲学时,他经历了敌机的疯狂轰炸,却泰然不动,谈笑如常……
他这样对自己的儿子解释道——
我心中何以能这样坦定呢?当然这其间亦有一种天分的,而主要还由于我有一种自喻和自信。
……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好大的口气啊!——但只有梁漱溟配这样说,也只有梁漱溟敢这样说。因为抗日战争需要他,建国大业需要他;他是真正地献策了,他是真正地出力了。他的自信,代表的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内涵;他的自负,蕴含的正是抗战胜利的力量之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