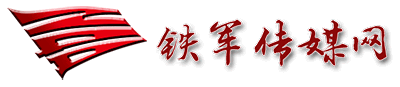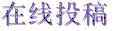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摩擦的标志性事件,一直是党史军史学界研究的重点事件之一。多年来,对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的研究侧重在中共方面,从国民党方面进行研究不够。本文想从蒋介石集团在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问题上的态度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新四军北移行动的影响作一些探索。
逼迫新四军北移的《中央提示案》出笼
国共合作抗日以后,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英勇作战,敌后抗日根据地迅猛发展。1937年8月下旬八路军改编,随即进至华北抗日前线作战,到12月底就从3.4万人发展到9.2万余人,1938年底发展到16万人左右。新四军进入大江南北敌后抗战时,全军只有1.03万余人,6200余支枪,但发展势头很猛。第一、第二支队很快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并迅速向北发展,进入苏北,造成了足跨大江南北的有利态势。第三支队创建了皖南抗日根据地,第四支队则向皖东皖西方向发展。从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到1940年底的两年多时间里,华中新四军对日伪作战24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5.1万余人,自身也发展到8万余人。
面对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根据地的发展,国民党蒋介石很是恐惧,在日军战略进攻基本停止,正面战场趋于稳定,日军将主要力量转到占领区对付共产党之后,国民党于1939年1月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研究对付共产党人的办法,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此后,国民党高层就如何根本解决共党问题进行策划,拟定了最后方案《中央提示案》,其要点有四:一、限区。“取消冀察战区,将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阎锡山仍任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朱德仍分任副司令长官。”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部“调赴朱副长官所负责之区域内(即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并将新四军加入第十八集团军战斗序列,归朱副长官指挥”。二、限编。第十八集团军“除编为三个军六个师三个补充团外,再加两个补充团,不准有支队”。“新四军编为两个师”。“师之编制为整理师两旅四团制”。三、取消民众武装。四、取消中共政权。这个方案蒋介石很快就批准了。
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国共两党开始进行谈判,国民党谈判代表将《中央提示案》送达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手中后,周恩来于7月24日飞延安磋商。延安方面虽不反对军事划界的办法,但根本无法接受这个让自己困死冀察的提案,所以提出以华北五省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区域的复案。蒋介石立即予以拒绝。中共方面退了一步,提出只增加山东及绥远之一部为作战区域,蒋介石仍然毫不通融。
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叶挺,要求“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所规定之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它各项规定切实遵行”。史称“皓电”。为了配合“皓电”,军令部秘密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确定第一步以第三战区兵力于1941年1月底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转用兵力肃清苏北新四军;第二步以第五战区兵力于1941年2月底前肃清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11月14日军令部将计划上报蒋介石批准。
在国民党的严令威胁面前,中共中央认真分析了局势,确定了对策,即“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方针既定,11月9日,中共便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出了致何应钦、白崇禧“佳电”,对“皓电”作出公开答复,驳斥了对方的指责,拒绝了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的命令,为了顾全大局,表示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
曹甸战役前,国民党方面规定,皖南新四军移动路线为从新四军军部驻地直接向东经苏南北渡长江,是为东线
新四军军部经过集体讨论,完全同意中共中央意见,决定“放弃皖南”,北移。从11月初开始,新四军军部就在认真考虑北移路线问题了。
军部考虑最理想的是走东线北移。因为东线相对北线(从新四军军部驻地直接北上,在铜陵繁昌地区渡长江北上)而言比较安全,皖南苏南联系比较多,没有发生过和国民党方面的冲突。而皖南和江北的联系就很不顺了,原因就在新四军发展华中的方针与桂系的利益起了冲突。新四军江北部队在桂系盘踞的大别山根据地东、西地区发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给正准备依据大别山向安徽敌后渗透的桂系以极大的不安。
1939年8月23日,廖磊向桂系领袖、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提出全面解决安徽境内共产党武装问题的办法,李宗仁于27日转呈蒋介石,主要内容有两点:第一,皖东北(淮北)不是共产党游击区,在那里活动的游击力量(主要有从豫南东进的彭雪枫部、当地发展起来的武装以及南下的八路军彭明治部及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拟请电饬调归建制,在指定游击区内活动”。第二,皖东虽是第四支队合法游击区,但是也要限制编制,“新四军拟成立第五支队,万恳不可批准”,并“拟请对该军械弹补充上,应予相当限制”。9月1日,桂系又制造了“鄂东惨案”,围剿共产党领导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五大队,共产党人被枪杀“百人以上”。
鄂东事件后,蒋介石与中共争夺华中的策略进一步明晰,即压迫华中新四军南调,取缔中共领导的华中地方游击队。1939年11月15日,蒋介石再电安徽当局敦促新四军正规军执行南调命令。12月7日白崇禧致电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要求江北新四军过江。1939年底刘少奇到皖东后,经过反复考虑,最终认为要坚决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力发展华中,必须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这样两党争夺华中的斗争日趋激烈,新四军与桂系的冲突也就难以避免。
鉴于以上形势,军部决定走东线北移,于是派叶挺去上饶与顾祝同谈判。11月6日,军部将此事电报毛泽东等。11月26日,顾祝同同意新四军军部北移路线为东线。当然,蒋介石、顾祝同这样爽快地同意皖南新四军从苏南北渡长江进入苏北,并不是想让皖南和苏北的两支新四军合为一股,而是想让新四军按照《中央提示案》的要求,下一步于1941年1月底前全部从苏北北移,到冀察地区去,从而达到根本解决华中问题的目的。
但是,在此期间,新四军领导人又研究出了一个“明走东线,暗走北线,分头北移”的方案,并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叶挺、项英没有想到的是,国民党方面突然改变了新四军北移的线路,从而打乱了新四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北移部署。
曹甸战役开始后,蒋介石集团下令变更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即从经过苏南北渡改为走铜陵、繁昌北渡
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是一个反共急先锋,曹甸战役前,他率所辖部队和新四军有过多次武装冲突。1940年9月30日,韩德勤不顾抗战大局,集中其大部兵力,向新四军驻防地泰州黄桥进犯。陈毅、粟裕以劣势兵力在黄桥地区同韩部决战。战役自10月3日起至6日胜利结束,共歼灭韩部第八十九军军长以下1.1万余人。新四军乘胜追击,进占海安、东台等地。黄桥战役后,韩德勤率部退守兴化、曹甸一线。此役重创了国民党韩德勤部主力,极大地刺激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高层领导人。但因战役是彼方发动的,政治上很被动,蒋介石集团无话可说。加之,新四军提出经苏南北移时,战役已经结束,所以为了顺利把皖南新四军赶过江,蒋介石也没有必要禁止皖南新四军走东线北移。
1940年11月,国民党驻皖东第二十一集团军七个团占领了津浦铁路以西新四军活动地区周家岗、界牌集等地。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所部会同由山东南下的第一一二师霍守义部,先后攻占了阜宁县西南的凤谷村、益林、东沟等地,企图接应第二十一集团军继续向东扩张。为保卫苏北抗日根据地,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于11月29日集中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第二纵队和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共10个团,对江苏宝应县曹甸地区的韩德勤部发起了攻击。战役历时18天,歼顽军8000余人,新四军、八路军伤亡2000余人。虽说曹甸战役是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苏北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东西夹击企图的重要战役,但毕竟是先发制人,政治上被动。
曹甸战役一打响(11月29日),何应钦就急忙于12月3日亲笔致函军令部长徐永昌,提出:为了解救韩德勤,“可令汤恩伯东进”,“对在江南之N4A不准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并要求将本意见“速签呈委座核示”。12月10日,蒋介石同意了何的提议,并下令顾祝同:“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规定路线亦可。”
蒋介石要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北移时改走北线,即经铜繁间直接北渡,纯粹是曹甸战役刺激的结果。如果没有曹甸战役危及韩德勤,蒋介石不会出此下策,因为蒋介石的目的是要新四军北移,中途改道,只会给新四军的拖延带来借口。
实际上,这个时候国民党命令新四军改道北线北移,这是对新四军北移突然性的毁灭性冲击。北移路线被公开后,日军和桂军都有计划地做了堵截部署,这样新四军从原地偷渡过江的行动就失去了突然性。项英见无法以突然性达成北移目的,于是又提出一北移方案:要求国民党方面在皖北让路,即桂系部队要让道,让出沿江渡口,如江北桂军进攻无为占据沿江渡口,“我军即不北渡”。要求国民党方面同意新四军部队北移时间再展期一个月,以便若断若续“分小批北渡”。随即,项英又请示中共中央,目前形势危急,北渡路线上困难重重,“我们的行动应如何?”
在新四军准备实施北移时,顾祝同同意可以一部经苏南走东线,主力仍经铜、繁走北线
中共中央在了解了新四军北渡路线上的危险和困难后,除了指示项英自己想办法有决心外,于12月25日致电周恩来,要求与蒋介石交涉,皖南新四军“须分苏南,铜、繁两路北移”。26日,周恩来即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他与蒋介石谈话的情况,关于北移路线问题,蒋介石是这样说的:“你们过,从皖北一样可过,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周注:靠不住)。”30日,毛泽东等致电叶挺、项英,转述了周恩来电报的内容:“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四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并表示:“我们同意恩来意见。”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和中共中央的意见,新四军军部去电三战区和顾祝同交涉,要求走“东线”北移。12月30日下午,顾祝同“准以一个团取道苏南北渡”。为了达到让皖南新四军早日北移的目的,顾祝同是尽可能地予以安抚与妥协,但他得按蒋介石的意思办,也就是说,皖南新四军主力部队还是要从原地直接北移的(走北线)。蒋介石坚持新四军皖南部队走北线北移,可能还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万一新四军过江后不北进时,必然要和桂系发生冲突,借桂系之手消灭新四军,是蒋介石很乐意的事。这也是蒋介石坚持新四军北移走北线的思想动机之一。
由于上述北移路线上的重重困难,新四军领导人始终犹豫不决。12月26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个给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三人的电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指出:“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在遭到了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后,28日,项英召开了新四军军分会会议,专门研究了北移路线问题,经过反复比较,最后决定走南线北移,即先从军部驻地云岭南下,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至溧阳,待机渡江。
皖南新四军北移时选择走“南线”,是新四军领导人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但是走南线是非常危险的,一是走南线没有合法的依据,且明显违反了蒋介石走北线的命令,也违反了顾祝同大部走北线,准以一个团走东线的命令;二是走南线是向第三战区腹地深入,一旦遇阻,非打不可;三是真打起来,政治上是被动的。
但现实太残酷了,12月底和1月初时,新四军领导人已经很清楚地了解到上官云相正在加紧调动部队,向云岭推进,准备完成对新四军军部的包围。军部领导认为,在其包围圈未成之际,立即迅速南下茂林,绕道三溪,经天目山脚下之宁国、郎溪到达溧阳,然后再伺机北渡,应有相当成功机率,所以才做出了冒险走南线的最后决定。1月1日,项英和叶挺向中共中央报告称:“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进,并采取游击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可能性很大,我们如遇阻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其后,项英还有专电报告中共中央,具体说明他们的意图“是先对南面包围我之顽军佯示威胁,吸引顽方注意,然后突然东进转向苏南”。
从1940年11月初中共中央决定在皖南取让步政策,决定皖南新四军全部北移开始,在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问题上,国共双方进行了两个月的博弈,但蒋介石国民党方面始终掌握话语权,皖南新四军总是处于被动适应的局面,开始先根据国民党走东线的规定进行种种准备,当国民党不准走东线,只准走北线后,又手忙脚乱,无所适从,最后选择了一条最不适宜的南线,结果使皖南新四军陷入绝境。